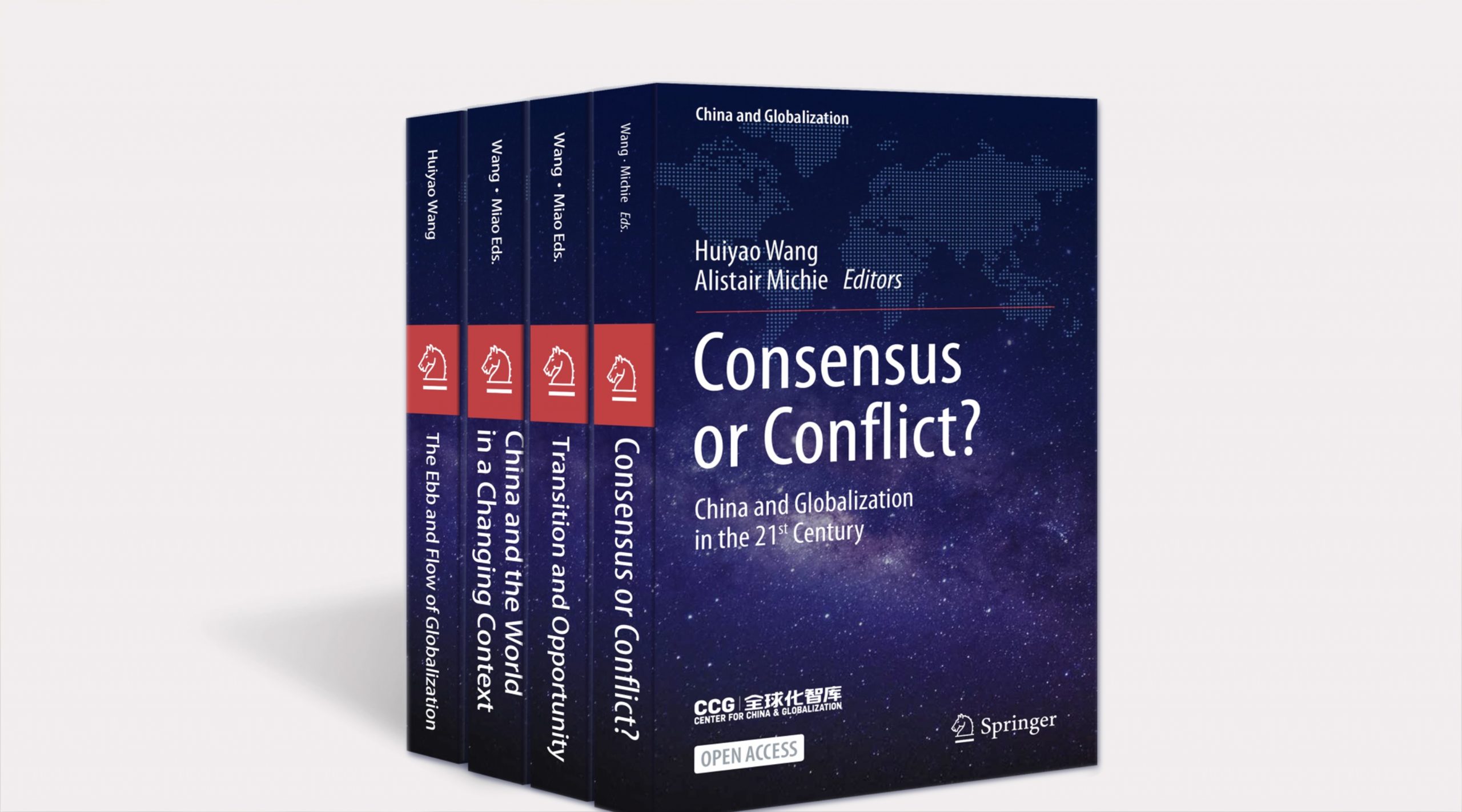中国该怎么吸引海外学者?
高层次人才多以事业为重,吸引高层次人才回中国的最佳方法莫如告诉他:“你的事业在中国”。这既是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的关键,也是中国吸引高层次人才回国目的之所在。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难的是如何创造能使回国人才真正实现在事业上大展鸿图的环境和机制。
近年已有许多留学人员回国工作。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目前归国人员中,去外企的多,去国企的少;去创业的多,去教育科研的少;欧洲回来的多,美国回来的少;毕业不久的多,高层次的少。其中,已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们到大学与国家科研单位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在去年的人才研讨会上我分析了产生这四多四少的原因[1]。回国人才去外企的多,是因为外企有“海外”的学术环境。回国人才去创业的多,是因为在中国创业有市场上的地方优势。美国人才相对于欧洲人才回国的少,是因为美国是移民国家,留美人员融入西方社会更深。高层人才回国的少,是因为他们更考虑工作环境,考虑是否能真正起到领军的作用。高层人才去教育科研的特别少,说明中国的学术环境已成为培养人才、引进人才的掣肘。目前中国海外回国人员已很多,缺的是科研人才,特别是科技领军人物。在中国中、长期人才战略发展不断推进之时,搞清楚什么是良好的学术环境,怎样建立良好的学术环境变得日益重要。本文就建立良好学术环境的三个基本问题:生活待遇、科研投资、成果评审提出了笔者的思考。
一、要让知识分子有荣誉感、成就感
建立良好学术环境的第一条应是弘扬热爱科技工作的精神,并提供一个让科技人员能够热爱自己的工作,全心投入于科学事业的环境。
最近系里给两个教授查尔斯(Charles)和彼特(Peter)庆祝80岁生日。查尔斯是我系的奠基人之一,从建系起四十年来总是一丝不苟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虽已退休多年,查尔斯仍然主管全系的教学安排,始终坚持上课。他对系里的工作是既出力又出钱,每年查尔斯对学校的捐款都远远超过学校给他的工作津贴。彼特身材清瘦,衣装入时,从后面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年轻人。更可贵的是他有一颗年轻的心。会上他谈起研究成果,一脸兴奋。我祝辞说他们代表了我校的精神,是我们的榜样。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校有70多岁仍在领导岗位上的院士,有80多岁仍在四处演讲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查尔斯与彼特都是在副教授职位上退下来的,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教员。他们没有鲜花簇拥环绕,也不追求大众的追捧,但他们热爱事业也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他们有荣誉感,大学教授是受人尊敬的职业;他们有成就感,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在他们的教诲下长大成才;他们有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人到80仍健步如飞,思维敏捷,仍能以自己的知识回馈于社会,做自己喜欢的事。人到如此,何欲他求。他们默默的奉献,是在良好的环境下对事业衷心热爱的表现。
从一个国家来讲,从一个学校来讲,应当如何培养这种对事业的衷心热爱呢?我们提到了荣誉感、成就感、和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我们要让知识分子有荣誉感、成就感,要让他们有所成;要弘扬热爱科技、教育工作的精神。生活条件、工资待遇固然要好。但只提薪资待遇是不够的。高层次科教人才追求的不是奢侈的生活。一心追求享乐之人怎么能拥抱寂寞专注于科研?中国政府提出的对人才提供“待遇适当,无后顾之忧的生活环境”的政策是十分正确的。那么什么叫待遇适当呢?在美国大学里,工资待遇的定位主要根据两项原则:贡献和市场价值。贡献好理解,以下我对市场价值给出进一步的解释。
在美国,同在一个学校不同专业的教授工资相差很多。医学院教授挣的最多,其次是法学院、商学院,再其次是工学院教授,最后才是文理学院的教授。工资上的差距不是学校有意的划分,而是与社会、工业界竞争的结果,是由各行业的市场价值来决定的。每个新人的任命,其工资待遇,除本人能力外,都还要考虑同行业工资待遇和本人的现有待遇。同行业包括同类大学和工业界相应的位置。久而久之,各专业的工资就与本专业的商业界、工业界的工资相挂钩了。因工业界各专业的工资相差很多,大学内各专业的工资距离也就拉开了。应当说明,工资最高的医学院的教授,往往学校只付其工资的一部分,甚至很小的一部分,其余部分是靠其在学校医院出门诊看病人等获得的。工资待遇有竞争性,这就是美国大学普遍采用的“待遇适当”的标准,也就是他们所说的人才的市场价值。
近年来许多跨国公司把它们的研发机构开到了中国,越开越多,越开越大。据统计到2010年3月为止,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已超过1200个[2]。这些研究中心的成立提高了中国境内的科研力量,提高了科研人员的市场价值,是件好事。但同时也要看到跨国公司积极地把其研发机构开在中国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是因为他们的工资待遇在中国有竞争力。
从国外引进高层次人才亦是如此。通过引进人才提高中国的竞争力,通过引进人才弘扬热爱科技工作的精神。二者并举才是人才引进工作的真正成功。
二、中国对科教投入仍需进一步加强
热爱科技工作的精神和生活环境是留住人才的基本条件,而良好的工作环境是让人才能够开创事业的必要条件。英语里有一句话:“Research transforms $ into knowledge. Innovation transforms knowledge into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科学研究是把钱变成知识。创业是把已得的知识变成更多的钱”。创业会有很多困难。但既然有商业利润在前,必然有投资人感兴趣,必然会给地方上带来种种可见的利益。基础性科学研究就不同了,研究结果大众分享,谈不上投资价值。商人不感兴趣。但科技水平代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实力。没有这个实力,知识自主和走到世界前列就无从谈起。所以国家、政府必须是科学研究投入的主力。基础科学必须走大众投资,大众分享之路。有了硬件条件,科研工作才可以有效的开展。中国近廿年来发展迅速,对教育科研投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所有的西方国家。很多科研单位硬件条件已经非常好了。但应当看到,中国的发展是非常不平衡的。中国总体来讲还是落后的。科教资金虽增长迅速,但在总额度及占国家开支比例方面仍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国家对科教的投入仍需进一步的加强。另一方面,在建造了一些与世界接轨的先进窗口之后,国家也应当考虑一下如何解决发展中不平衡的问题,考虑一下如何进一步扩大基础提高总体实力的问题。
在美国经济一片哀声之时,2009年10月德克萨斯州议会决定拿出5亿美元来增强几所大学的研究能力[3]。这笔称作国家研究性大学基金的钱,每年会增多,但最后各个大学能拿到多少要以其成绩来决定。引人注目的是,此资金不资助德州排名靠前的三所大学,只资助属于德州第二梯队的其他七所研究性大学。这种做法初看起来令人十分不解。因为,即使是德州最好的公立大学——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在全美大学排名也在40名以外[4]。如此分配基金,德州如何能争第一?但仔细想来,德州要争的是整体实力的提升,看的是加州有九所一流大学(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纽约州有七所,德州这个全美人口第二的州,却只有三所一流大学。此基金一出,第二梯队有了新的动力,第一梯队有了新的压力。各校纷纷行动,促动了学校之间的竞争。不管最后哪几位胜出,德州的总体实力必将增强。
德州在各州纷纷削减教育经费之时,逆势而上,追加投资,扩大第一梯队,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扩大基础,提高总体实力,以期取得新突破的想法值得借鉴。其实这种以点带线的做法,大家都在做。各州都有自己的重点大学,各校都有自己的重点学科,但往往在重点形成之后,大家想到的大多是如何保住重点,很少有考虑如何缩小点与线的距离,以线推点,提高整体实力。
点与线的关系值得好好研究。点是线的带动,线是点的基础。没有点,线会停滞不前;没有线,点也会后劲不足,难以为继。从国外引进高层次人才亦是如此。要人才配套,以高层次人才带动人才,以人才推动高层次人才,形成梯队,使大家在事业上都更上一层搂。如果点是个人,线是集体,良好的学术环境就是让真正有创造性的个人层层出头,形成学术之宝塔。科研上需要个人的一点突破,工程上需要集体的全线告捷。突破与告捷频频而至,中国科技的总体实力就会在这突破与告捷之中一步步增强。学术之宝塔长得够高了,中国就成了科技强国。中国要科教兴国就先要凝聚住一大批叫人肃然起敬的科技英才,要在大学与大学、学科与学科、科研与教学、个人与集体、行政与业务等各方面处理好点与线的关系,在竞争中不断有所突破,在竞争中不断提高整体实力。
三、科学成果审核需制度化
钱再多也是有限的,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让真正有潜力的知识分子出头,脱颖而出,一定要搞好科学成果鉴定,搞好科学项目审评,让创新性人才真正能发挥作用。
从原则上来讲,科学成果的鉴定非常简单,就是看其是否在科学上有重要贡献,有没有影响力(impact)。基础科学的研究影响力主要表现在拓广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工程项目的研究影响力主要表现在提高了人类生活的质量。鉴定的难点是这影响力难以量化。有人用研究资金的多少来衡量研究成果,这是不对的。研究资金是根据研究项目的需要而给的,与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往往没有直接联系。有人用经济效益来衡量研究成果,但经济效益并不等于商业利润,否则中国的房地产老板都应当成为院士了。有人用文章的数量来衡量影响力,但这显然也是不够的,因为文章的数量不能说明文章的质量。有人把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分成三、六、九等用以衡量文章的质量。虽然这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同一本学术期刊里的文章质量也可以相差很多,同一个档次的期刊总体水平也大有不同。有人用文章的引用率作为文章的影响因子。开创性的文章引某一领域之先,理应多被引用。但在实际中,综述性文章引用率也很高,甚至高于开创性文章。总之,有很多指标可以作为衡量研究质量的参数,但一旦把这些参数公式化,作为提职、提薪和科学成果鉴定的硬性指标,有些“聪明人”就会跟着评定公式做科研。如果总是让这些“聪明人”走在前面,领风气之先,真正开创性的人才还是难以出头。
如果科学成果不能用任何一个公式来量化的话,那么什么才是科研成果评定的最好方法呢?笔者认为最好的方法其实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专家评审的方法。但是,要使专家评审行之有效必须做到两点:“找对人”和“敢讲真话”。“找对人”指的是找的专家确有能力,包括业务能力和精力,能够做好评审工作。“敢讲真话”说的是专家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科学出发,无所保留。前者可以通过专家推荐专家来解决,后者是专家评审制度成功与否的关键。专家评审的失败,往往都是请来的专家只说些不痛不痒的话,或存有私心,真话不全说。要让专家敢于说真话是需要一些制度保障的。要做好专家评审,笔者认为需要做到下面几个方面:
1.后顾无忧
科研从本质上讲是少数人发现多数人不知道的规律并推翻现有理论的一种特殊工作。因不同而创新。如果没有制度保障,专家说话之前先得想一想是否会被下岗,自然就没人敢说话。解除后顾之忧是搞好科研成果鉴定和建立良好学术环境的必要条件。
2.排除干扰
既然是专家评审,就要听专家的意见。干扰之下会出大错。最突出的例子是仍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美国中央情报局本认为伊拉克没有毁灭性杀伤武器,时任美国副总统西尼不甘心,亲自到中央情报局坐镇两天“帮”中情局的情报员分析情报。“帮助”的结果是中情局证实伊拉克有毁灭性杀伤武器。当然,众所周知,这个在总统压力下产生的情报分析是错误的。一条压力下产生的错误情报分析为一场劳民伤财的战争提供了导火索。干扰专家的正确判断危害之大由此可见。
3.确保公正
排除干扰只是搞好专家评审的必要条件,要真正做到公正还需要更多的制度保证。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设有许多措施用以保证评审的公正性。笔者归纳总结成以下几条:1)匿名性:评审者姓名保密,专家审核小组的名单也不公开。2)随机性:并没有固定的专家组,每个小组委员会都是临时组成的。3)多样性:专家小组尽量选不同背景、不同层次的专家组成。4)专业性:小组讨论,就事论事,一人一票,一视同仁。5)流动性:为了避免项目主任的喜好影响科学研究的发展,大约近一半的科基委的项目主任是从学术界和工业界来的短期轮换工作者(2-3年)。6)开放性:除了固定的资助项目外,每年科基委都根据公众的需求提出一些新的特别研究项目。成功的特别项目会融入现有的固定项目,以此达到了项目的逐步更新。7)不固定性:虽然都是专家审核,但对不同的项目,审核程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8)公开性:所有基金支持的项目,并包括这些项目的进展报告,都要在网上公开,以利于大众监督。9)自动回避:科基委有明确规定什么情况下评审人必须回避。在各个单位、各级专家评审中,大都有自动回避这一条。回避制度从另一个角度保证评审的公正性。
建立良好的学术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牵扯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错综复杂、千丝万缕,并且表现的问题在不断变化之中。三十年前是工资低,三十年后是房价高;三十年前是吃大锅饭,三十年后是官本位。更复杂的是大家的认识有时并不一致。近年来虽然中国的学术环境一天天好起来,但离中国科教兴国战略方针的要求还相差甚远。笔者在此文中也只做到了以一代十,以有限的例子给出有局限性的思考,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大家对学术环境更多的关心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