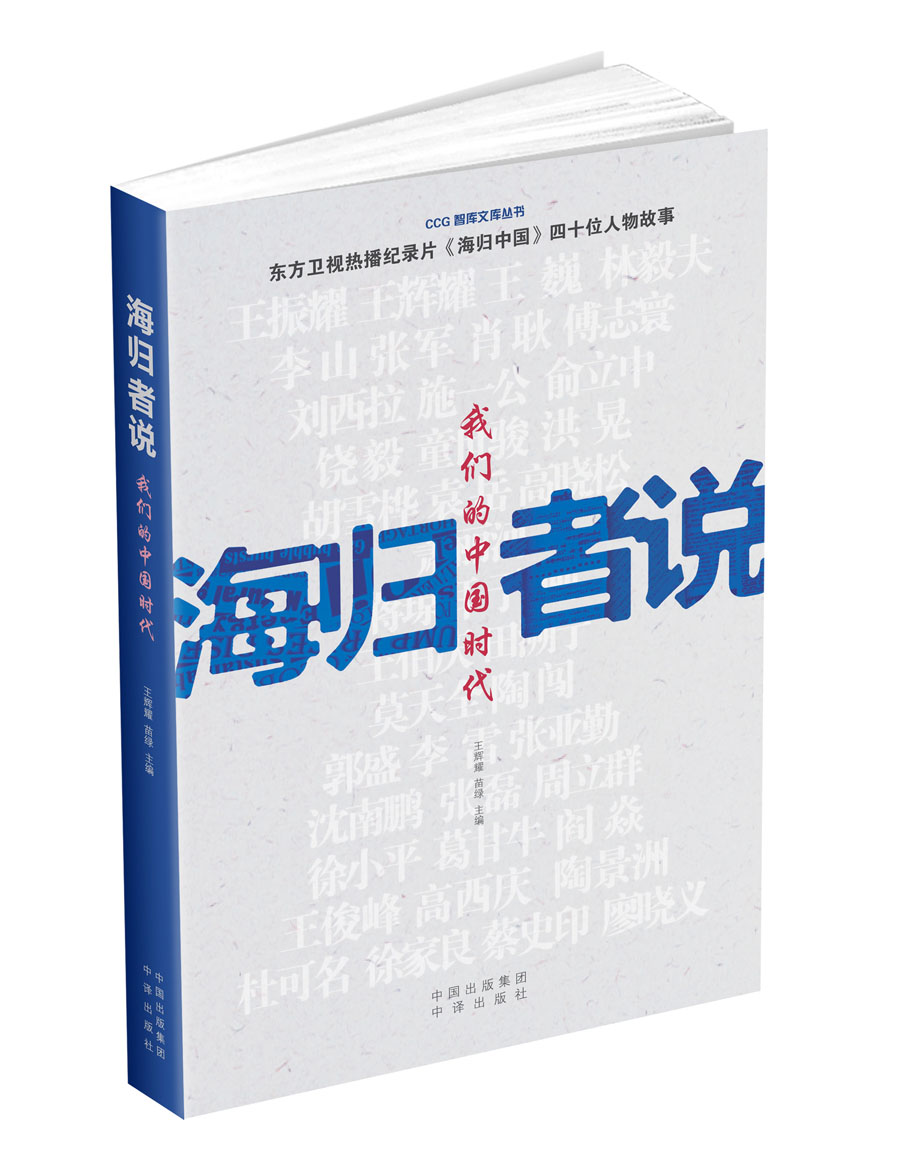徐小平:信念的力量
2016年1月25日
我们那代人是在精神食粮相对匮乏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我对知识和文明有强烈的求知欲。改革开放前,我只能从有限的资源,如《唐诗三百首》《离骚》等中汲取知识。那时,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回乡,其中有我的音乐启蒙老师何冰和其他一些中学老师,虽然书籍匮乏,他们仍给我们讲述了不少的名著和典故。残缺不全的教育和强烈的求知欲构成了我们那代人独特的人格–对知识、文明、外部世界、新鲜事物都充满渴望。1978年恢复高考,我们欣喜若狂,压抑了多年的求知欲似井喷海啸般迸发。我如愿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
五年大学毕业后,我到北京大学艺术教研室当了一名教师。在北大期间,我和俞敏洪、王强关系最密切。一起吃饭,一起过节,相互照顾。我们渴望留学并付诸行动,王强学过英文写作,帮我打国际长途,但那个学校并没录取我。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时,文化部曾有公派出国名额,但我没得到机会。
有两年时间,我日夜想着出国,做梦都跟出国有关,曾梦见在国外泳池游泳。我赴美之路充满艰辛,不仅有护照签证问题,也有政府间的人为隔阂,阻力很大。因此当克服重重困难,来到美国的一瞬间,我非常激动,犹如发现新大陆一般。出国实属不易,耗尽精力、时间、金钱和家人的期待,但这种经历为我日后在新东方做留学项目提供了经验。
说起来,我在美国从未真正立足过。那时,留学生梦想拿到学位,找到工作,买房买车,接父母出国,而这在当时是奢侈的。我太太硕士毕业得到一份年薪六万美元的工作,而我却屡屡受挫,压力很大。我曾到加拿大找过机会,也尝试回国发展,但都没有得到预想的效果。曾有人建议我做房产经纪或者考执照,找份工作,但我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之所以未在北美立足,我总结出了三个原因。一、专业问题。我是学音乐教育的,本就很难就业。二、我的梦想。太太曾建议我读法律,但我不感兴趣,我还是想读文学,读艺术。三、心存祖国。我觉得中国的机会多,我可以施展才能的天地也大,我想创建公司,想做电视节目,想做娱乐界的大腕,所以我才在1992年回国探索创业。
美国星河灿烂,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但我并未为之所动,而是追求自己最喜欢、最擅长、市场需求最大之事。这个方向从未改变。比如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我被分到上海文化局,离家虽近,但我婉拒了。因为我被北大吸引,要矢志不渝追求喜欢之事。村上春树曾说:“作家写作时身上有毒素,排出毒素,小说才能成形。”于我,这不是毒素,而是灵魂中最甜蜜的东西。于是,我1992年回国,1993年创业。如今,我在创作《中国合伙人2》,表达三个人创业成功的过程,这让我很快乐,找到了生活的理由。我从未放弃自己,一直想回国,改变中国文化,希望成为启蒙式人物。不论一无所有还是腰缠万贯,无论是处于令人羡慕的留学生之位还是经历创业的惨败。即使众叛亲离,也未曾忘记自己的梦想。我相信每个人都要怀疑自己究竟是谁,这能时刻提醒自己该朝着哪个方向发展。
1994年创业失败后,我回到加拿大,写剧本、传记,在所谓的文化界鬼混。准备回国前,俞敏洪到北美考察,他的到来为我回国提供了最完美的平台。他曾说,“这么多年,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如今想想二十年前的俞敏洪与现今相比,天差地别。1995年,他是个体户,如今新东方代表着中国民营企业万紫千红的春天。他接纳了我,在新东方,我的喜怒哀乐、挫折、渴望都得到了完美的释放。
在新东方,俞敏洪上课讲他的苦闷,王强上课讲他的成功–北大校园领袖和美国实验室,我讲学生的悲惨以及咨询我之后成功的过程。由于在国外多年,了解出国流程,我为新东方的学生提供留学服务,做得很精彩。其实,俞敏洪、王强和我三人就完美地构成了一个人奋斗的精神链条:首先要学好新概念、大学四六级等基础英语,再考托福、GRE出国。而我们三人,王强负责讲基础英语,俞敏洪教托福、GRE,我则提供出国服务。所以我们在产业链上也配合得很完美。
做留学要与众不同。我不会问对方是否能出国,而是考虑他该不该出国,出国将给他带来怎样的人生价值。有时,甚至有点刻意避开生意的目的,打造他的个人潜能。人生的选择和设计是新东方的精神,这奠定了新东方品牌里极其闪光的一部分。我们既做牌坊,也立牌坊。我的如是举措在于新东方给了我信任,我要对得起俞敏洪。
后来,新东方上市了。它变得和其他企业不一样,这让我们充满了精神上的愉悦。正如松下说的:“要电器像自来水一样大批量生产”,松下每生产一个电吹风、一台电视机,便实现了一次突破。新东方的学生从一个到一百个也是一种突破。新东方上市后,突然闲下来,使我很有挫折感。我常批评俞敏洪,三驾马车本可以继续奔驰在祖国大地上,但上市后我们的工作转变了。如今,我每天谈项目,把所创造的财富打出去时,依然在播撒新东方的种子和梦想。我们并未摆脱从前的心态,充满好奇心、渴望、参与欲,希望证明自己,从未变过。
随着新东方等留学机构雨后春笋般得在中华大地上萌芽,短短的十几年间,中国的留学生数量呈几何倍数上升。留学生带来了普罗米修斯之火,他们用西方文明之光,照亮了伟大而古老的中华文明中某些未被现代文明照亮的角落。中华文明若能恢复当年的恢弘与辉煌,就能与世界最强的国家,在硬实力、软实力、吸引力上抗衡媲美甚至实现超越。
2009年,我首次到哈佛论坛做演讲,其中提到生长在中国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回中国寻找人生,但要认清怎样实现自我,你的能力在哪里能最大限度地放光。当时,我并没说这个地方是中国。但每年去做演讲,主题就一个:回到彼岸,寻找你的家。这个家毫无疑问是中国,即使雾霾笼罩着北京,但有远见的人能看到一个晴朗的明天。
文章选自《海归者说-我们的中国时代》,主编:王辉耀/苗绿,中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