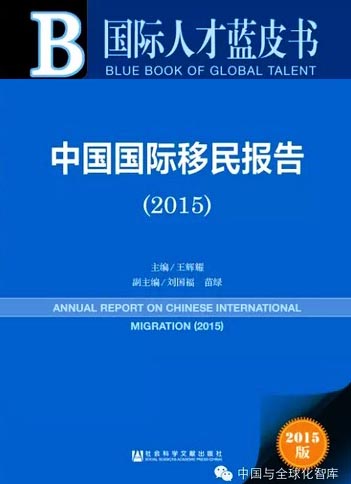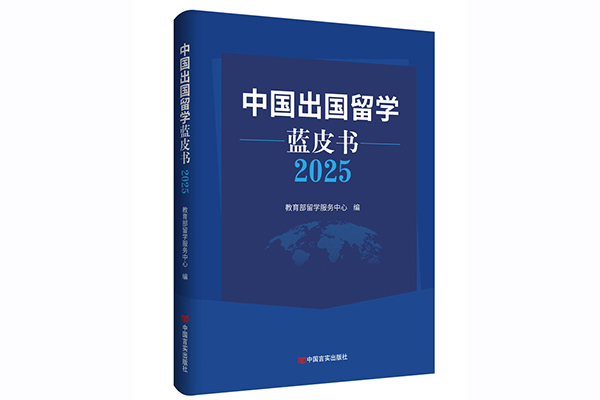美英法日大都市区外国人管理之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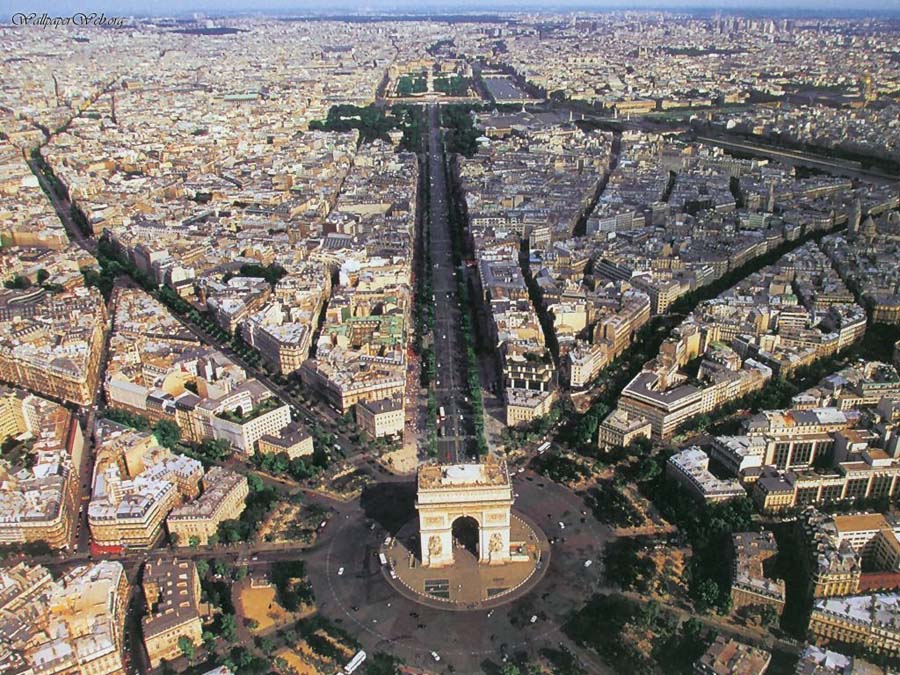
外国人管理与服务,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特点。发达国家国内任何一个城市或乡镇,在向国际大都市(都市区、都市圈)发展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一些固有的难题。宏观而言,需要对本地或跨地域的外国人管理与服务内容进行跨界协调;微观而言,则需要从本地具体情况出发,设计适合本地发展的外国人管理策略与方案,并且力求解决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外国人管理的命题,意味着不断地利弊权衡和权利均衡。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国家移民的种族、民族和其他人口统计学属性上看,国家层面的移民法已无法体现国内地方和大都市区的移民特征。由于劳动力市场是移民迁徙的重要原因,而劳动力市场主要聚集在大都市区,因此,将大都市区作为主要分析单位,更能呈现移民的变化特征。本文首先从美国的大都市区谈起。
(一)美国大都市区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国内的城市化进程无不与移民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自美国1776年建国以来,就不断出台和修订关于外国人管理和服务的法规,包括《外国人法案》、《外国人登记法案》、《移民与国籍法》等,其条文数量和繁杂内容堪称世界之最。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进入城市郊区化阶段,亟需实行大都市区一体化管理。美国的中心城市对郊区实行兼并,之后进入郊区化扩散阶段,郊区通过合并独立建市,使得地方县市镇政府数目繁多。50年代后期,地方政府又强化大都市区政府的权威,很多地区成立了大都市区顾问委员会。 70年代之后,美国进入所谓“逆城市化”的“后城市”阶段,采取了突破“单核”布局限制、主动在城郊之间构建多个次中心、打造国际化大都市区的创新方案。
1. 美国大都市区移民分布情况
在20世纪80—90年代的移民潮中,多达1千万人的合法与非法移民得以入境,其中有85%以上是亚裔或拉美裔移民。 1992年,美国共有282个大都市统计区(MSAs),3.3万个县、市、镇和特区地方政府,平均每个大都市区都有117个地方政府单位, 这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地方行政管理最分裂的国家之一。 新移民与国内流动人口的剧烈变动使美国国内地方人口结构呈现“巴尔干化(balkanisation)”的特征。当移民人口抵达目的居住地后,在基本的生计条件满足的条件下,会习惯性地同与自己宗教信仰、文化习俗和语言传统相近的群体生活或交往,于是在大都市区中,出现了许多相对独立的移民“飞地(enclaves)”。
按照国外移民迁入人数、流动人口迁入人数和流动人口迁出人数划分,美国各州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国外移民迁入主导型,包括加州、纽约、德州、新泽西、伊利诺伊和麻省;第二类为流动人口迁入主导型,包括弗罗里达、乔治亚、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华盛顿和亚利桑那州;第三类为流动人口迁出主导型,包括路易斯安那、密歇根、俄亥俄、奥克拉荷马和爱荷华州。
2. 洛杉矶模式与路易斯维尔模式
有学者将美国大都市区按地方政府的相互关系分为两类: 一是较少合作型,包括纽约、洛杉矶、圣路易斯等大都市区;二是合作协调型,包括路易斯维尔、华盛顿、匹兹堡、迈阿密、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杰克逊维尔等大都市区。 前者易形成单一职能的特区,后者则易形成大都市管治委员会,两种模式分别体现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多中心模式和区域主义合并倡导者的一体化模式。 两种模式都是基于本地具体情况采取的优化方案。
(1)洛杉矶大都市区的多中心协调模式
联邦移民局(即公民与移民服务局,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USCIS)为外国人事务的主管部门。 美国对外国人事务的审批权集中在联邦一级,所有签证申请均要送至联邦移民局下属的五个移民服务中心,分别位于西部的加州、东北部的佛蒙特州、南部的德州、中西部的内布拉斯加州和密苏里州(现名全国福利中心)。
加州移民服务中心(California Service Center, CSC)位于奥兰治县(Orange)的拉古纳尼古尔市(Laguna Niguel),共有六个部门,分别为就业案件分部、家庭案件分部、客户服务分部、安全与防欺诈分部、运营策略分部以及资源管理分部。中心经费4%来自财政拨款、96%来自申请费,大量邮件及财务单据接收、分类及转运工作由外聘合同工完成。 联邦移民局在每个州设有移民分局,各移民分局受理本地移民、签证申请。所有申请由各移民分局和境外使领馆(负责境外移民和签证申请)寄送五个移民服务中心审批。
位于加州南部的洛杉矶大都市区,由于政治分化、经济结构和种族矛盾,长久以来并没有形成区域内的联合机构,而是通过一些跨行政区组织,如南加州政府联合会(SCAG),在联邦和州相关立法的推动下,为其赋予了独立于政府的地位。在外国人管理与服务方面,难度最大的就是跨文化交流与冲突化解工作,而这些工作通过缺乏协调的政府部门分别处理,很难收到较好的效果。而通过以某些具体行业或治理主题建立起来的跨行政区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克服洛杉矶大都市区政治分化、经济剧变和种族矛盾的瓶颈, 更有针对性、更为有效地解决外国人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跨行政区组织承担了洛杉矶大都市区多个治理中心之间的协调者。
(2)路易斯维尔大都市区的市县合约模式
与洛杉矶大都市区不同的是,由肯塔基州4个县和印第安纳州南部4个县组成的路易斯维尔大都市区,采取的是以路易斯维尔中心市和杰佛逊中心县达成合约的方式开展的治理模式。这种一体化程度更高的治理模式之所以能够实现,与两个重要原因密不可分:一是郊区化过程中路易斯维尔市流向杰佛逊县的人口带走了大量就业税;二是1985年路易斯维尔市长斯劳恩(Harvey Sloan)担任杰佛逊县县长,与同为民主党人的新任路易斯维尔市长阿布拉姆森(Jerry Abramson)通力合作,推动签署了两个地方政府间的12年期合约,将大都市区的12个机构在合并后的联合机构中进行了新的安排:大气污染、健康、犯罪和规划四个机构分配给杰佛逊县;灾害、应急服务、人类关系、历史和科学博物馆及动物园分配给路易斯维尔市;图书馆、公园、运输和地下水系统保留给联合机构。(Ibid.)这使外国人管理与服务能够在联合机构的统一协调下,为大都市区设计更为合理的机制安排,能够在提高效率的同时,避免可能出现的地方冲突。
(二)伦敦大都市区
伦敦大都市区最早的城市形态是伦敦城(City of London),面积仅为1平方英里。作为公共政策与法治内容范畴的外国人管理,传统上被认为是政府这一民族国家的主要行为体承担的义务与责任,但20世纪70—80年代,福柯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概念产生,强调政府存在的意义不止于立法、行政和司法,而应把提高福利、改善生活、积累财富、保障健康和延长寿命作为终极目标。 在单纯依靠政府难以提升现代化进程中外国人管理与服务这一公共物品(以下简称“公益”)提供的效率和质量的时候,伦敦大都市区在企业型政府和公私合作领域迈出了领先的步伐。
1. 济贫税保障移民福利
16世纪早期,随着英国人口增长及经济变革的推动,伦敦外来移民人数增长迅猛,移民问题日益恶化,教会主导下的济贫体制不足以救助越来越多的无助贫民。外来移民的混乱无序,就引起了以“政治共同体”(commonwealth)思想家和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为代表的知识阶层的关注。16世纪40年代以后,伦敦市政当局就济贫资金的募集方式和济贫工作管理方法进行的重大调整,就体现了“法治”与“救助”两相结合的方案。1547年,市政议会通过决议,通过财产评估向市民征收救济金,建立强制性济贫税税率,相当于市民个人收入的1/30,通过五家慈善救济院实现对济贫工作的管理,这一政府保障国民福利职能形成的成为政府现代性的重要标志。
18世纪30年代以来兴起的英国工业革命,促使英国人开始思考城市与郊区之间的关系,在《1855年大都市区管理法案》基础上建立的大都市区工作委员会,已初步具备了伦敦大都市区地方治理机构的雏形。
传统的伦敦城法团和教区委员会缺少协调、各自为政,对城市外国人管理与服务供给极为不利。伦敦大都市区治理体制的变革需求由此产生。中央政府曾成立专门的皇家委员会,负责大都市区治理方案的制订。这一方案的内容大多体现在英国议会《1888年地方政府法案》和《1899年伦敦政府条例》中。
2. 地方尝试治理新模式
伦敦大都市区在19世纪上半叶初步成型之后,实行的是“大伦敦市政府—自治市议会”双层治理结构,两级政府之间是合作而非隶属关系。各自治市的地方政府结构也从传统的委员会制变为“议会—经理制”、“市长—内阁制”和“领导人—内阁制”中的一种。1979年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赢得大选后,对地方政府治理结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传统的地方政府的角色和职能进入了“碎片化”的地方治理结构模式。20世纪80年代,为应对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和公共服务质量欠佳的“英国病”,撒切尔首相大胆推广国企私有化和政府中介化,选择效率高的运作方式,削减公共预算。 伦敦大都市区建立了一种政府部门、私人部门和志愿组织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新的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s)治理模式,推进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模式,旨在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
(三)法国大巴黎计划
2005年10月,在巴黎东北郊的克利希瓦镇(Clichy-Sous-Boi),两个移民少年因躲避警察追赶触电身亡,引发了法国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骚乱。持续三周的骚乱波及德国和比利时等国家,给整个法国和欧洲造成了严重影响。很多人认为这是法国移民政策的失败,但实际上此次事件暴露了巴黎的城市空间分隔与社会分化危机。 这一判断体现了中医的全息疗法思路:将病体首先调整到一个自然平衡的状态,在激活人体自身免疫力与内分泌功能的情况下攻克病患。法国的“大巴黎计划(Grand Paris)”,就是决策者在本国移民管理出现漏洞的情况下,反思城市规划和机构当中的弊端,进而通过改革移民管理体制、推进大都市区振兴计划,而开展的一系列打破城市与郊区之间藩篱的大胆举措。该计划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1. 多元治理中的协调中心一体化
2007年5月,法国新任总统萨尔科齐上任后,成立了法国史上首次在政府机构中设立主管移民事务的“移民、融入、国民身份与共同发展部”,旨在对法国由外交部、内政部、社会事务与就业部、司法部、边防警察中央局民警和国防部军警(法国国家宪兵)多部门共同管辖外国人事务的情况加以整合。 该统一管理举措,有助于在多个部门中确立一个协调中心,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与此同时,位于巴黎的各政府部门下属众多与外国人管理事务相关的咨询机构、民间团体、社会公共服务组织和协会,急政府之所急、想政府之所想,协助政府解决外国人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协调中心的“一”和治理主体的“多”是法国外国人管理的主要特征。
2.推动移民个体能力建设
2007年秋,法国总统萨尔科奇设立了“首都地区拓展事务”国务秘书职务,具体负责巴黎未来20—30年的拓展振兴计划,即“大巴黎计划”该计划以打破隔离、促进融合的思想以及“跨界规划”与“跨线设计”的思路,为拥有1.2万多平方公里地域、约1500万人口的大巴黎地区提供了十种弥合城郊分化的方案。大巴黎地区由巴黎市区、近郊三省及远郊四省组成,由于长期以来行政管理上的分隔和空间发展上的分离,城市与郊区的两极分化严重阻碍了巴黎作为法国经济与文化引擎作用的发挥。法国的行政建制分为中央、大区、省和市镇四级,但其城市规划体系却没有据此形成法规体系,于是导致城市总体规划失效以及城市空间畸形发展,隶属外省的郊区因缺乏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长期得不到发展。 在从整体上打破城郊隔阂的同时,大巴黎都市区又采用了“外法内仁”的移民能力建设。这一全息疗法的思路在对于非法居留自愿回国者,会提供一份安置费;对于家中有两个孩子的家庭,自愿回国补助金额度为6,000欧元。对于逃避或企图逃避遣送出境的行为,处以3年监禁、最多十年不得入境的惩罚;对以假结婚骗取或帮助他人骗取法国居留或法国国籍的行为,可处以5年监禁和15000欧元罚款。
(四)东京都市圈
东京都市圈包括东京、大阪、名古屋三个城市圈。东京作为三大城市圈之首,是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聚集体之一。1952年4月,日本恢复了因身为二战战败国而由美国为首的盟军司令部掌控的外国人管理权,并在1947年5月《外国人登记令》基础上制定了《外国人登记法》。1989年12月,在1981年《出入境管理令》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并于1990年6月1日正式实施。 2004年5月,日本众议院出台了《出入境管理法修正案》,力求缓解非法居留问题。近年来,以《外国人登记法》和《出入境管理法》为基础的日本外国人居留管理制度,又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在借鉴美国和英国大都市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东京根据“大都市否定论”与“大都市肯定论”数次改进都市圈规划。
在狭小的空间中取得令人瞠目的经济成就,东京大都市圈可谓是空间极度集约型利用的典范。 无论是从人口地域的发展演变、产业结构的时序演变、还是地域结构的演化过程来看,东京大都市圈的建设过程都是有代表性的。空间和结构的集约体现在机制的集约与地方自治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补充。东京的外国人管理与服务,体现了从政府主导、半官半民、向官民合作与互补、多元主体参与的良性进程。
1. 中央—地方合二为一
由过去中央和地方二元化管理体制转变为由法务大臣为核心的一元化管理体制,实现中央事权的高度统一,是以先进的信息共享机制为支撑的,而先进的信息共享机制,又是在充分运用高科技综合信息数据库和果断废除1952年《外国人登记法》、发放IC居留卡的配套举措下实现的。 东京大都市圈乃至日本全国在大力推进出入境管理信息公开透明的过程中,实现了事前入境审查、事中居留管理和事后出境审查三个阶段的信息通过IC居留卡随时由法务大臣掌控的一元化管理,外国人的指纹测定、面部摄像和所有能够实现身份识别的信息,都可以通过居留卡便捷地查询。这些信息是与居民基本信息系统相互联动的,能够保证相关各方对外国人进行全方位跟踪。
与中央与地方的外国人集约管理相辅相成的,是地方社区微观单元的自主治理。1991年,日本国会正式将以家庭(户)为单位加入的町内会作为“地缘群体”写进了《地方自治法》的附则中,使其获得了法人资格和民间地位。这使自下而上的市民自治与自上而下的集中治理能够相互补充,有助于实现使异质性相互包容的共生纽带。
2. 外“堵”内“赶” 引进人才
日本2004年的《出入境管理法修正案》采用的是外“堵”内“赶”的思路:对非法居留者的罚金从30万日元提高为300万日元;凡因非法居留被逮捕者,不再收容居留,而是尽快遣送回国;曾有过非法居留记录再次非法居留者,禁止入境5-10年;留学生退学后3个月未找到正式工作者,命其离境。 与严厉的非法居留规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政府对于访问、留学和就业的外国人提供的便利的管理服务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居留期限从3年延长至5年,1年内再入境不必重新办理手续;其次,简化留学申请程序,有步骤地延长一次性签发留学签证的时间;第三,促进外国留学生在日本就业,并提供安定的在留环境。
对于高等教育留学生来日学习和就业的开放态度,是日本在外国人管理制度中的优点和亮点。留学生当中的高层次人才,是各国人才战略中争相吸引的对象。然而,外国人能够对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贡献,其具体的审批标准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在日本,该标准是由法务大臣来做判断的,在批准与否的问题上,法务大臣握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但由于日本通过IC居留卡实现的信息共享,帮助法务大臣能够较对外国人的数量、结构和分布领域有全方位的把握,使其能够更为客观地分析哪些“高精尖”人才能够满足国家或地方发展过程中的需求,从而按对国家事业贡献的多少,给予优厚待遇,扩大海外人才的储备。从这一角度来讲,以信息公开为特征的“阳光管理”为日本外国人管理与服务提供了更多的“善治”工具,使其能够在外国人管理领域开创业绩。
五、对我国的启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办理居留证必须交健康证明书、护照、签证和与居留事由相关的证明。在各部门缺乏协调的情况下,“与居留事由相关的证明”就会带来因多头管理、各自为政而出现的冗长和繁琐的审批过程。比如,以一名来京担任外教的外国人为例,需要出具聘任书、外国专家任职通知书、由北京市劳动社会保障局签发的劳动就业许可证、以及市教育局、市劳动局、外国专家局等国家行政机关签发的有关证件。因办理这些证件既费时日又延误时间,从而造成“三非”问题的情形时有发生。此外,将“三非”人员遣送回国有一定难度,有些难以确定国籍,有些则因缺乏遣送经费造成公安部门实际操作中的困难。 由此可见,外国人管理与服务质量,往往是公共治理能力的一种体现。为提升我国大都市外国人管理与服务水平,笔者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向美国两大都市区学习多中心与一体化经验
洛杉矶与路易斯维尔大都市区分别作为多中心和一体化治理模式的代表,都是根据本地具体情况历史形成的现实最优模式选择。在联系相对疏离的地方,难以建立区域内的联合机构,则通过跨行政区组织对具体领域的外国人管理与服务内容进行协调。对于地方行政区划之间相互依赖程度较高的地方,当有政策创业者或企业家有意推动时,一体化的程度就可能提高,相应的协议才可能签署和有效执行。以上两种方案,并不意味着前者的跨行政区组织建设难度就比区域内联合机构的组织难度小。二者都是在大都市区多元行为体的利益与责任之间寻找均衡点的路径探索,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但每一种成功路径的实现,都不是被动得来的,而是利益相关方的志愿推动和相关公共部门的支持与配合互动作用的成果。
向伦敦学习公私合作制
公私合作关系(PPPs)是20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为克服“政府失灵”提出的公共治理思路。 伦敦大都市区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成为首先采用这一治理思路的地区,与其历史上尊重知识、重视法治、关爱弱势群体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外国人管理与服务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城郊融合、国企私有化、政府中介化等公私合作治理模式,会带来一系列过去没有先例的挑战与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进行解决本身,就是一种“公益”。政府在采取此种治理思路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不理解、不认同、不合作,而转变观念所需要的耐心、细心、决心是否足够,是决定公私合作制这种新治理模式能否成功的关键要素。外国人管理与服务是嵌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进程的专项工作内容,但在全球化和国际化发展迅速的今天,很多时候可能会成为引领其他公共治理内容追随其脚步共同发展的引领事业。
向巴黎学习全息疗法
外国人管理中“三非”问题的出现,往往需要采用系统化的整体思维去分析原因。北京境内的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问题,要在尽量问清造成外国人不遵守我国出入境法规的个体原因的同时,判断究竟是外国人自身的原因、还是我方制度中存在不足,从保护外国人权益的角度,给出更为全面合理的分析、解答和化解。
向巴黎学习全息疗法,意味着在考察“三非”问题出现原因的时候,可以跳出被侵权者的视角,思考如何通过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更好地使外国人感受到北京城市规划和制度设计的合理性。正如当人们正视“中国式过马路”现象时,发现那些闯红灯的群众原来也有难处,红绿灯的时长设置、红绿灯置放方式,往往成为有法不依的重要原因。
向日本学习集约型管理
日本式管理在20世纪80年代风靡全球,其原因除了日本经济在70年代初期的高速发展外,更重要的是其人本主义管理理念。日本大都市圈的集约型管理精髓,也是人本主义。将个人之“私”融入治理之“公”,需要具备对个体信息进行记录和测量的高科技手段,辅以对创新知识的尊重和对外来人才的珍视。管理的核心,是让人去做事,而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将事情完成到何种程度,则是因人而异的。科学管理强调的是量化考核与绩效评价,而进行信息和数据的积累、统计与分析,则需要专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这样的投入是值得的,因为无法测量的公益,是不可持续的。在外国人管理与服务方面,也需要这样的智慧,去解开公益提供难以持续的难题,给个体以创新和实干的激励和动力。
本文选自《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主编:王辉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