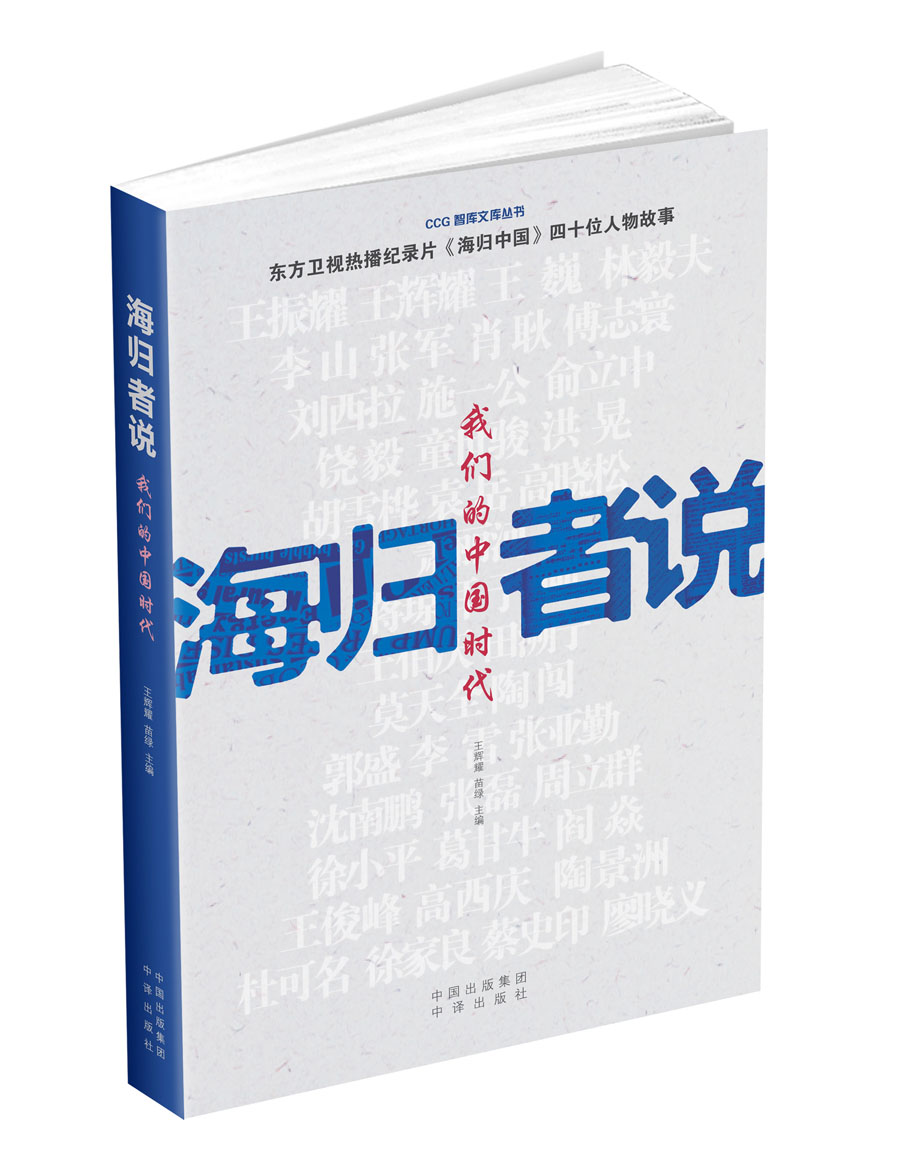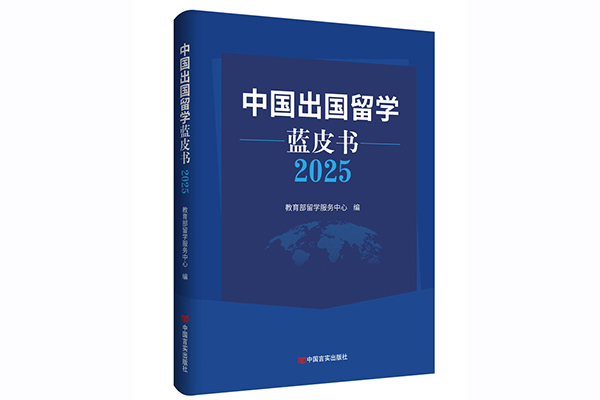高晓松:流放自我,收获辽阔

▼
我是八八级毕业生,也是最后一届公费生,毕业后要服从国家分配,分配到哪儿去哪儿。当时,每班留京名额只有两个,大多数人都被分配到其他省的城市,也有人被分配到边远地区。争取留京名额付出的代价并不比出国小,而且国内外差距明显,所以大家都特别想出去。后来,国家颁布了一个严格的文件,要求公费生为国家做出五年贡献后才能申领护照,有直系华侨亲属或者旁系华侨亲属的除外。直系华侨亲属可以直接出国,旁系华侨亲属要交国家培养费,差不多一年2500元,清华本科是五年,总计交12500元。而毕业后做公务员,每月才赚72元,12500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没有直系或旁系华侨亲属的人想出国就更没有希望了。
那时候出国赚钱很容易,学生刷盘子或做服务员,每年差不多能挣一万美元,当时汇率为八点以上,相当于八万元人民币,而国内的公务员每年才赚八百元。面对这样巨大的差距,大家都拼命想出国,大批的大三学生退学出国。没有直系或旁系华侨亲属背景的人想出国就必须大三退学,因为只要完成学业就必须依照国家规定服务五年才能拿到护照出国。但学校为办理退学的学生保留学籍一年,以确保万一拿不到签证或奖学金可以继续上学。我母亲在德国出生,所以我是直系侨属,不用服务国家五年,而选择退学是随大流,也实在是不想上学了。退学后父母给我办了自费留德,并保留学籍一年。本来就不想读了,结果退学就会使原来五年的本科又变成了六年,那就更不想读了。
出国时,想法很简单,只想学个手艺,赚钱养家。我在清华读的是无线电系,录取分数是最高的,但毕业分配是最惨的,因为当时IT行业还没有兴起。当年我们系的同学毕业后,很少从事相关专业工作,我读的是雷达专业,更不好找工作了,所以决定转行。其实家人把我的一辈子安排好了,就是完成清华学业,然后出国留学,而我觉得与家人走一样的路,没有一点意思,所以自费留德一直是个备选。我在心里决定不留学,做一些家人不懂的事情,所以才选择不会跟家人沾上半点关系的电影和音乐。
后来决定出国读书,是各方面影响的结果。当时我们全班总共34人,出过国的人数最多时高达17人,缴纳班费时大家都交美元。我一直在国内学习生活,而家里所有人都走留学这条路,自己好像一个土鳖,心里总觉得缺失一块儿。1996年,我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举行了自己的作品音乐会,事业发展得很好,但家里没有人到现场看,对他们也没有什么触动。再有就是曾经在清华有一个关于读书无用论的讨论会,家人也参与了,现场有位教授提出:高晓松就是读书无用论的典型代表。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后来决定把这一课补上。
每个人年轻时都会很激进,不仅是思想方面,情感上也激进,觉得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大事。即使音乐流派之争,都觉得很严重,睡不着觉。但走出去看一看,会让自己变得更平和,每到一个地方先去看海,坐在海边,自己慢慢就会辽阔起来。我还把小时候所有音乐里写过的、读书过程中发现的以及画中的地方都看了一遍。有趣的是,到了巴黎圣母院,我先围着墙转了一圈找字母,寻找小说里描写的刻在墙上的字。看了才发现,其实对这些地方挺熟悉,因为如果没有一首歌、没有一部文学作品提到他们,那他们不是那个样子。当时看了一本书《流放回来的人们》,讲聚集在巴黎的各国艺术家,互相熏陶、碰撞,过着流放的生活,之后带起整个世界的故事。为了这个目的,我觉得自己应该流放一下,到处走一走。
目前,我还没有真正回国,在洛杉矶有很多工作,正在做一部英文的音乐剧,在电影方面也是中美两边都涉猎。美国还是有很多人才,尤其在我们这个行业,经历几十年积累,大量人才活跃在百老汇、好莱坞、拉斯维加斯等的舞台上。而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使中国的经济总量有一天超过美国,但中国的电影、舞台剧、流行音乐是不会超过美国的,周围的人还是热衷于美国的流行音乐、电影大片、音乐剧。好莱坞、百老汇欢迎全世界的人参加,美国通过绿卡吸引全世界其他国家艺术学院毕业的人,为他们提供融合交流的平台。科技和文化都需要不断沟通融合,而且文化交流与国家富有与否没有根本联系,比美国富有的国家很多,比如沙特阿拉伯或者科威特,但世界各国导演很少去这些地区。所以,这个行业在中国的发展还需很长时间。
选择中美两边工作,对我来说最重要。一个人一生做了多少选择或者选择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有权利选择。也许我没做别的选择,就唱一首歌,爱一个人,但是我要有权利选择。就像一个国家,不能不允许离婚,每个人都要到一个有选择权利的地方。自由被很多人提倡,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辽阔。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多一种语言,多一种文化,多一个圈子,多一个行业,多一个国家,就会多一分辽阔。
文章选自《海归者说-我们的中国时代》,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CCG主任王辉耀,中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