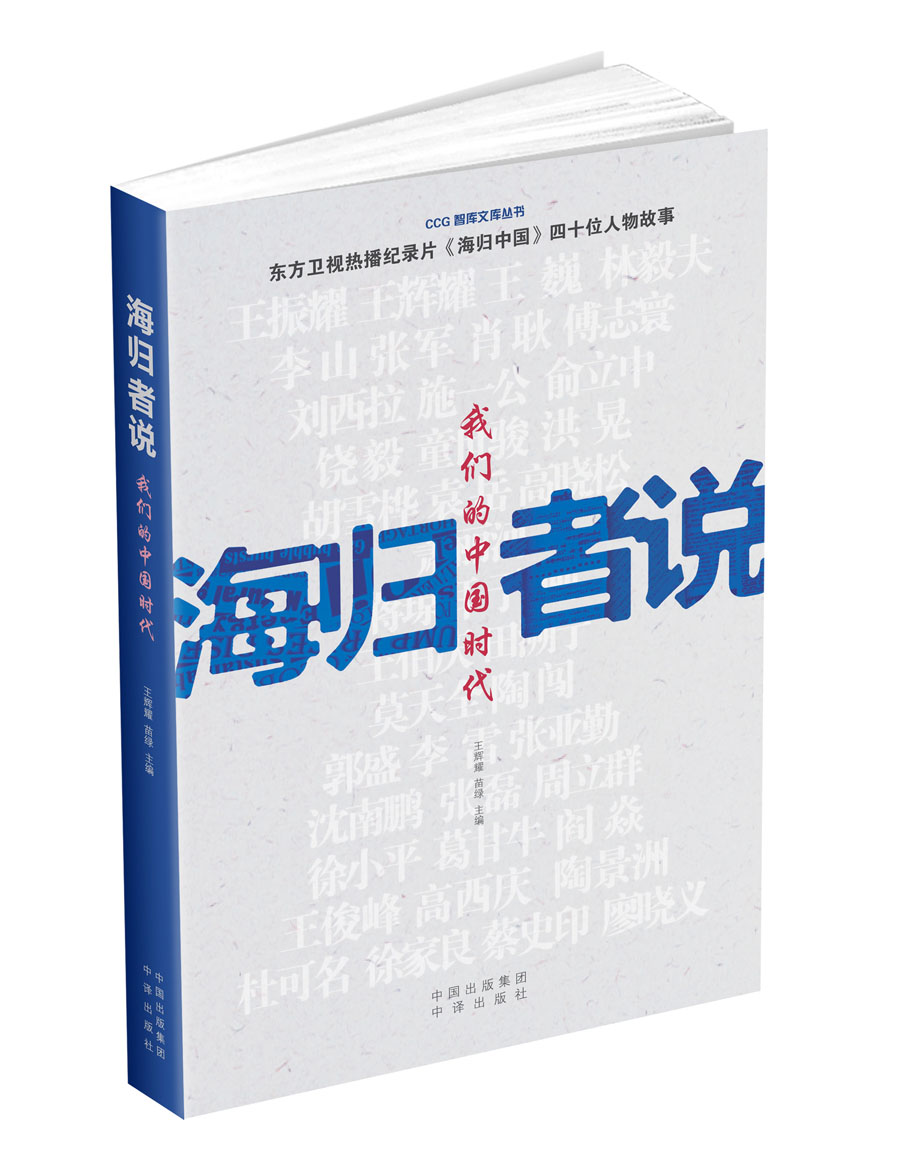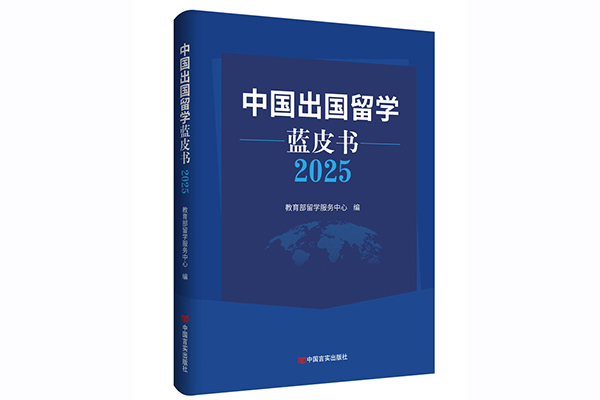徐家良:中国的公益慈善

▼
现在大众对公益慈善的理解基本停留在捐钱帮助困难的人群层面,而且做公益慈善是不能赚钱的。如果公益组织不赚钱,他的钱从哪儿来?一般都是别人捐的。他自己没有造血功能,捐款用掉之后又要找人捐。但有些公益慈善组织像国外的学校基金会,他就会去投资。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美国高校基金会受到的损失非常大,投资回报率低了很多。因此,很多私立学校后来就采取多招留学生,降低奖学金额度,减少奖学金数量,缩减工作人员来弥补损失。
实际上,目前的法律没有规定公益组织不能进入哪些投资领域。公益组织是独立的法人,法人只要能够自己承担风险就可以投资。我们基金会条例里面有一个规定就是保值增值,只要做到保值增值就可以投资。我们投资的是股票,其他的基金会也有股票投入。期货的风险很大,目前的基金会可能没人进入,因为它来得快去得也快。
社会企业与公众认知的公益组织有所不同,他是运用企业的运营方式实现公益的目标和使命。企业最早是从欧洲社会经济的概念衍生过来的。后来英国大使馆在中国创导了社会企业家培训,2009年时,开始形成一定的规模,每年有上百人接受培训,这对推动整个社会企业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而且,社会企业的发展与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刚好可以衔接起来。有些社会问题是政府解决了,有些社会问题是一般的社会组织、公益组织解决的,一些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正好可以用社会企业的方式来解决,效果肯定更好。
目前,中国的社会企业越来越多,虽然与其他的社会组织相比,数量上可能会少一点,但与前几年相比已有了很大的增长。
社会企业或者公益组织与商业企业之间虽然有边界,但并不是很清晰,也不应该清晰。我一般用圆圈来比喻他们的关系,比如说企业是个圆圈,社会组织也是个圆圈,这两个圆圈原来是独立的,没有交集。但是,在大量的过程当中,这两个圆圈就有了交集,连成了一块。比如说社会组织有一些活动需要企业捐赠,这就有交集了。现在,社会企业之间的交集是:有的是企业有捐赠,有的用企业的运作方式去赚钱,然后来解决社会问题。在原来的计划经济时期,公益慈善基本上就是花钱的,不是赚钱的。现在,情况不同了,公益或者慈善领域有不同的类别,有些组织确实是靠捐赠,自己不赚钱也是可以的;有些则不靠捐赠,而是通过自己的造血功能赚钱,然后用在公益慈善领域。社会组织的不同方式对整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是很有帮助的。
现在,中国引入了一些国外的公益模式,这些模式,有的发展得很好,有的可能要稍微调整才能适应中国的国情。
2007年,我到台湾去,看到有一个基金会投标了台北市政府手里的几个加油站。基金会投标可能比一般的商业企业价格要低一点,但有一个条件是他雇佣的人群是残障人士。其实这个模式非常好,增加了残障人士的就业渠道。残障人士没有工作,一是会增加家里的负担,二是对他自己来说没有与社会接触的机会。而台湾的这种模式给了残障人士工作的机会,同时也能够为社会、为公众带来很多好的效果。国外慈善公益的模式,能够为中国公益慈善的发展提供更丰富的社会组织的形态,更多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
在借鉴国外模式方面,海归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实际上,从海外回来的一些人,在不同的领域里面也都在做这一块。例如在环保方面做的比较早的就是梁从诫,最初他到国外去开会,接触到环保组织,之后在九十年代就与别人联合创立了自然之友。廖晓义也是到北卡罗来纳州留学归来后,办了地球村,拍了很多环保的电视纪录片。当时,海归人员基本上是在做环保宣传,但后来慢慢就变成了践行者。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廖晓义是环保使者,四川地震之后,她又到彭州地震灾区去搞乐和家园,把环保、节能和人们的美好生活连在了一起。廖晓义在彭州选了两个村做乐和家园,把环保、生态的理念带了进去,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对当地的管理体制也产生了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原来我们是比较宽泛的环保宣传,现在则是将环保聚焦到了某个地方。
对我们的整个社会来说,环保是比较欠缺的一块。一批人到国外去,意识到了环保的重要性,学到了国外的经验,回来也开始做环保。但当时的社会对他们的行为是不理解的,响应者也比较少,因为整个经济发展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还没有显示出来。后来,响应的人慢慢多起来,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老百姓的观念也改变了,经济发展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也显示出来了。社会对环保组织、环保人士的认同度也在提高,原来感觉他们很另类,饭都没吃饱,还要环保。现在饭是吃饱了,环保却严重透支了,要去补。
环保虽已成为社会共识,大家都知道经济发展对环境产生了影响,但对影响的程度却没有概念。汪永晨搞了两个活动,江河十年行和黄河十年行。他每年去考察,要连续考察十年,去了解黄河和长江流域环境的变化。2010年,我参加了江河十年行,考察长江。2011年,我又参加了黄河十年行去考察黄河,到黄河源头去看过之后感触非常大。黄河源头的环境比较脆弱,黄河的中下游地区,工业污染也很厉害。有些事情,人们看过之后,才会有更直观的印象,也会慢慢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
文章选自《海归者说-我们的中国时代》,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CCG主任王辉耀,中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