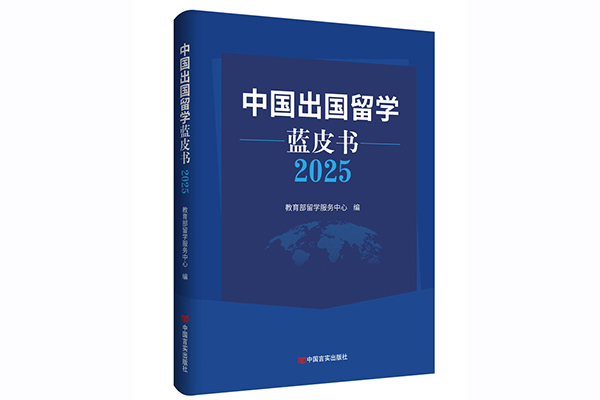智库研究输出机制 | CCG研究
智库凭借高质量的研究影响国家政策。这种影响会借助出版物等形式产生,因为研究成果在面向社会发布的同时,也会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从而帮助塑造政策和引导公众对某些议题的思考。
著作出版
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具备深厚的学术积淀,他们出版的著作常被业内奉为经典。比如约瑟夫·佩克曼(Joseph Pechman)所做的关于联邦税收政策的书,曾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帮助布鲁金斯学会确立了税收政策议程。令我颇为感叹的是,布鲁金斯研究人员在撰写著作方面的笔耕不辍,每隔几年,就会有新的著作诞生,比如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的《中国烟草的政治版图》、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的《未知的海峡两岸关系的未来》。布鲁金斯学会拥有自己的出版社,2015年度学会出版社共出版著作38本,学会大楼内还设有书店,出售出版社出版的著作。
“就像布鲁金斯学会一样,CFR同样有着浓厚的出书文化。”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副主席Jim Lindsay说,CFR鼓励智库的研究员们多写书。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始人弗雷德·伯格斯滕也经常建议研究所的研究员,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努力做到写书与短期政策项目并行。
以书籍形式推出智库成果,着眼于长期、宏观的影响力塑造,属于长线产品,一般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和精力,对不少智库来说,可能是一种“奢侈”。不过,事实证明,书籍的舆论影响力可以跨越时空,这种形式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更为深远。
刊 物
1970年,美国正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沼无法自拔,国内反战声浪此起彼伏。来自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P.Huntington)与其前哈佛同事沃伦·曼谢尔(Warren DemianManshel)认识到,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再审视和再定义”的时间到了,于是他们共同创办了《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在创刊词中,他们这样写道:要使这份杂志“严肃而非学术化,活泼而不圆滑,批判但不消极”。很快,这份杂志便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家园。1978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成为该杂志的所有者和发行人。1997年,委内瑞拉前经济部长莫塞斯·奈姆(Moisés Naím)成为杂志主编,在这位经济学家的引领下,《外交政策》影响与日俱增,不但先后多次获得全国杂志奖,还发行了阿拉伯语、日语、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等诸多版本。
《外交》(Foreign Affairs),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著名刊物,自1922年创刊以来,该杂志已成为美国重大国际事务的权威观点发源地。被称为“冷战”时期“遏制”理论之父的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就曾署名“X 先生”在《外交》上发表文章,为美国政府的对苏“冷战”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发表在《外交》上的《文明的冲突》,曾在国内外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IISS)出版的《军事力量对比》《战略研究》等刊物名气也非常大,常被推崇为世界军事方面的权威。
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曾主导的《外交政策》、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旗舰刊物《外交》、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Washington Quarterly)与《国际问题》杂志、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加拿大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国际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这些学术刊物之外,意见杂志也成为很多智库的选择。比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评论》(Brookings Review)、兰德公司的《兰德评论》(RandReview)、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美国企业》(The American Enterprise)、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的《弗雷泽论坛》(The Fraser Forum)等。
知名智库多有国际公认的刊物与杂志,智库成果可以通过这些平台得到发布与传播。可以说,通过创办刊物的方式来扩大影响力,基本成为知名智库的重要选择。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新的杂志将不断诞生,已有一段历史的杂志将呈现出出版周期缩短、出版频率增加、出版物数字化等发展趋势。
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刊物所需投入的财政资源也与日俱增,这些都超出了一家智库的能力所及,因此,2008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将《外交政策》出售给《华盛顿邮报》公司。
报告与论文
发表报告是智库经常采用的一种传播形式,比如兰德公司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与论文已超过13000篇。相对于著作的“费时费力”,报告形式相对灵活,对于增加智库的曝光率、赢得话语权,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渠道。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出版的年度报告《RAMSES》发行量达到1万份,在全世界都具有一定的影响,成为很多国际问题研究者观察世界格局走向的重要参考。
为了吸引工作忙碌的政策制定者的眼球,传统基金会另辟蹊径,采取了一种简洁快速的研究发布方式即政策简报。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还要归功于该智库的创办者,他们多在国会工作过,因此深谙“国会工作之道”:国会议员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每天只有非常有限的时间吸收思想,这就决定了能够概括现有研究的一篇文章可能比一本长篇巨著有用得多。尤其是在国会辩论期间到达的一篇分析报告比最终投票后才姗姗来迟的一本书更为有用。
智库的报告如何才能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呢?
发布时机很重要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率先就美国次贷危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等问题发表研究论文,引起世界广泛关注,所长伯格斯滕的论文《美元与赤字:美国如何避免下一次危机》更是引起全球轰动。
研究领域很关键
以反腐败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透明国际,在全球反腐败研究以及政策制定领域内都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该智库主要通过“全球腐败指数”来评估各国的腐败情况。1995年,透明国际公布了首份清廉指数报告,此后,这份年度报告经常被各大权威国际机构引用。从“纯洁绿洲”[2]方案到国际腐败洞察指数[3],透明国际在国际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研究质量需保证
1994年,一篇题为《中国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的崛起》的报告被推荐给有关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作为决策参考。这篇报告是由来自日本、美国和德国的三位作者为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所撰写。报告从启动到完成经历了大约一年时间,多次讨论,数易其稿。
电子时事通讯
互联网时代,智库开发了用电子出版物的形式来提高传播速度和广度,电子时事通讯就是其中一种,它以电子邮件的方式传达给受众和利益相关者,与平面媒体制作相比,传播成本低廉,时效性强,成为咨政、启迪大众的重要途径,受到很多智库的青睐,成为智库对外传播的发展趋势之一。比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就出版了包括《国际经济报告》周刊(International Economic Bulletin)、阿拉伯语和英语双语的《阿拉伯改革报告》月刊(Arab Reform Bulletin)、中文的《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防武器扩散信息》周刊(Proliferation News)等在内的6份电子时事通讯。
本文选自《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苗绿、王辉耀 著,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