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引发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例如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使得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
- CCG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
- CCG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
- CCG一带一路研究所
- CCG世界华商研究所
- CCG数字经济委员会
- CCG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图片
- CCG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图片
- CCG世界华商研究所图片
- CCG一带一路研究所图片
- CCG数字经济委员会图片
- 成为系列论坛会员
- 成为系列论坛会员联系
- 概况介绍
- 兼职研究员
- 未分类
- 概况
- 全球化
- 全球治理
- 美国
- 国际人才政策
- 中美贸易
- 国际教育理念与政策
- 中国开放指数
- 新闻动态
- CCG品牌论坛
- 中国与全球化论坛
- 学术委员会专家
- 主席/理事长
- 中文图书
- 品牌论坛
- 研究合作
- 重点支持智库研究与活动项目
- 概况视频
- 主任
- 香港委员会名誉主席
- 关于
- 团队
- 国际关系
- 国际组织
- 加拿大
- 华人华侨
- 国际贸易
- 来华留学
- 区域与城市
- 媒体报道
- 二轨外交
- 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
- 高级研究员
- 资深副主席
- 英文图书
- 圆桌研讨
- 建言献策
- 概况手册
- 副主任
- 理事申请
- 香港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 顾问
- 研究
- 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
- 区域合作
- 欧洲
- 中国海归
- 来华投资
- 出国留学
- 大湾区
- 活动预告
- 名家演讲
- 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
- 特邀高级研究员
- 副主席
- 杂志
- 名家演讲
- 媒体采访
- 年报
- 秘书长
- 企业理事
- 香港委员会主席
- 国际顾问
- 国际贸易与投资
- 一带一路
- 亚洲
- 留学生
- 对外投资
- 国际学校
- 动态
- 名家午餐会
- 中国人才50人论坛
- 特邀研究员
- 理事长
- 媒体采访
- 文章投稿
- 副秘书长
- 活动支持
- 香港委员会副主席
- 国际教育
- 非洲
- 数字贸易
- 活动
- 智库圆桌会
- 常务理事
- 智库访谈
- 国际合作
- 总监
- 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
- 研究员
- 研究支持
- 香港委员会常务理事
- 国内政策
- 拉美
- 专家
- 理事
- 直播
- 捐赠支持
- 主管
- 中国国际教育论坛
- 个人捐赠
- 前瞻研究
- 澳洲
- 咨询委员会
- 企业理事
- 其他
- 捐赠联系
- 中东
- 成为理事
- 研究报告
- 建言献策
- 出版物
- 理事申请联系
- 智库研究
- 音视频专区
- 联系我们
- 观点
- 捐赠
- 工作机会
- 香港委员会
-

国际移民发展新特征 | CCG研究
摘 要 近年,国际移民 发展趋势呈现出以下特点:国际移民数量增加,所在区域相对集中,但流动性下降;经济发展刺激短期迁徙;移民流动形式多元化,尤其在大规模移民流中,迁徙的动机具有很强的混合性;被迫流离失所者规模巨大,重新安置与返乡者的比例较低,但增幅开始出现放缓迹象。主要西方国家近年反映出的政策收紧趋势并不能反映政策变化的全貌,各国根据自身发展,在移民政策变革上各有侧重。劳务移民、就业与创新,一直处于移民政策争论的中心位置。美国与英国虽然不断加高投资移民的门槛,却特别制定了吸引企业家移民的政策与规则。在移民政策“收紧”之外,新加坡为增加人口规模相对放宽移民规划,加拿大结合国际教育战略增加了高素质移民的数量。虽然中国大陆地区国际移民占总人口比重仍是世界最低,但中国也在不断从国际移民来源国,成长为治理方式与机制不断进步的国际移民目的国,外国人“来华逐梦”也呈现上升趋势。“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也成为中国规范移民的重要流向地区。 国际移民发展呈现新特征1.国际移民数量增加,但区域相对集中,流动性下降 绝大部分国际移民更倾向于在出生地大陆迁徙,形成洲际地理区域划分上的相对稳定,洲际流动性下降。(如图1-7)欧盟作为对移民最有吸引力的地区之一,也呈现出欧盟国家内部的人口流动增长要快于非欧盟国家迁入欧盟的速度。国际移民的目的地也相对集中,2015年,67%的国际移民集中居住于20个国家。接收移民数量最大的国家为美国(4700万),接收近世界移民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19%);德国和俄罗斯为世界移民的第二大接收国(1200万);第三位为沙特阿拉伯,有1000万迁入移民。 人口寿命的延长与移民返乡的减少,也一定程度上促使国际移民的流动性下降。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迁入移民的寿命也和移民目的地的人口一样,寿命不断延长,体现在人口存量上就表现出移民人口数量的相对稳定或增长的趋势。例如2000年到2015年,移民人口的净增长对北美和大洋洲的人口增长贡献率分别为42%和32%。返乡移民数量下降,常规移民和难民返回来源地的数量越来越少,导致迁徙与返乡的环流迁徙趋势下降。这两种趋势都让目前国际移民的流动性逐渐降低。从数据上看,生活在非出生地的人口是按国际移民的存量来计算的(除非移民返回到自己的来源国家),这种统计方式不考虑移民是否想获得移民目的国国籍。 国际移民流动性下降的现象在OECD国家表现得比较明显。从1995到2014年这20年时间里,迁入OECD国家的永久性移民一直处于较为显著的增长态势,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增长较快。金融危机后,虽然永久性迁入移民的数量有两年的短暂回落,但很快又恢复增长。 2.经济发展刺激短期迁徙,收入与迁徙意愿成驼峰曲线关系,恰当的外援或能降低中长期迁徙的预期 如果有机会,世界16%(大概7亿)的成年人会选择去往另外一个国家。但真正成行的,只占有意向出国者的1%(700-900万)。社会经济因素既会成为驱动人们去往海外寻求更好机会的动因,同时贫穷、不平等、缺乏基础设施和失业这些情况,也会成为限制迁徙的因素。因此,收入与迁徙之间会形成一种驼峰曲线关系,即,极度穷困的人缺乏经济基础迁徙,但随着经济发展,年均收入大概进入7000-10000万美元的区间时,人们迁出原住地的能力与倾向开始增加。 经济发展状态良好的高收入国家,是侨汇的主要汇出地。由经济发展所决定的中短期工作机会,例如餐饮服务业、季节性农业工人激励着国际移民的短期迁徙。美国几十年来都是侨汇汇出金额最多的国家,2015年汇出金额达613.8亿美元;沙特阿拉伯位的侨汇汇出金额为387.9亿美元,位居第二;瑞士为243.8亿美元,位居第三;中国比较特殊,虽并非高收入国家,但已经以204.2亿美元的侨汇汇出量位居第四;第五大汇出国是俄罗斯(197亿美元)。 侨汇,从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侨汇汇出国对非永久性移民的吸引程度,当移民在海外安家后,会将侨汇汇入自己的原籍国,这些侨汇收入既是一国劳动者去往其他国家短期工作谋生的动力,同时还能够为改善家乡的生存环境贡献力量。因此,移民迁出本身会成为较贫困的国家,增加国家收入、支持经济发展的战略。官方的发展援助需要政府机构和政策制定者之间进行复杂的协调,而侨汇却可以便利、直接地到达需要的收款人手中。侨汇具有稳定性,而且已经证明其在经济下行时有助于经济复苏。随着居住在海外的人越来越多,侨汇汇入量也在增加,已经成为官方援助(ODA)金额的三倍。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如果官方的海外援助能使受援地区人民的收入达到收入与移民关系的分水岭,那么迁出的中长期移民有望降低,而转为选择短期迁徙。 3.迁徙途径的多元化与混合迁徙动机的移民流 纵观世界移民史,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国际移民的迁徙途径开始越来越具有全球性、流动性、连接性和长距离性,迁徙的方式与原由也变得更加复杂。这是移民目的国、来源国家、所在地区、种族和宗教背景、文化与语言、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多样化的结果。在国际移民潮中,不但有常规移民,还有难民与寻求庇护者等被迫迁徙者,甚至被贩运者。迁徙动机不仅限于获得工作机会、更好的社会福利和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还包括逃离危及生命的战争、暴力与自然灾害的侵害,进而影响移民在迁入国获得的法律身份与社会融入,还给移民与迁徙管理增添复杂性。例如当前混合迁徙现象显著的欧盟,能为经济移民提供的合法迁徙途径越来越受限制,但违规入境和居留的趋势却越来越高,以提交庇护申请来获得合法入境和居留身份者也越来越多。这使得欧盟花费大量精力去抑制非常规移民,而非加强升级发展管理完善的合法移民渠道。 自然灾害所导致的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也是导致人口境内迁徙,甚至国际迁徙的主要动因。海平面的上升、气候变暖、水循环的破坏形成的干旱与洪水越来越频繁,对粮食作物的毁坏直接导致了大量人口生存愈发艰难。2008-2016年环境灾害每年导致2530万人流离失所。由于例如飓风、洪水、泥石流、森林火险以及干旱等极端天气一共造成1.96亿人逃离家园,这些数据虽然只涉及境内流离失所者,但因此导致的人口跨境流动仍在继续,数年前在撒哈拉南部非洲爆发的干旱就导致了上亿人跨境迁徙。 4. 被迫流离失所者规模巨大,但增幅放缓,重新安置与返乡者比例较低 截至2016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达到6560万人,其中获得难民身份者225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4030万,还有1000万无国籍或处于无国籍风险之中的人。2016年新增流离失所者1030万,包括新增的境内流离失所者690万,和340万新增难民与寻求庇护者。有55.22万难民在2016年返乡,18.93万难民得到重新安置,分别仅占难民总量的2.45%与0.84%,仍然处于较低比例。截至2016年的数据表明,2016年的新增被迫流离失所者数量为30万人,相比2015年增数量580万人、2014年新增数量830万人,增幅出现放缓。这与非洲地区重大自然灾害的缓解以及因叙利亚冲突造成的潜在危机迁徙者减少有关。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随之产生的被迫迁徙潮对欧洲产生巨大影响,随后的数年,虽然欧洲的难民危机一直最受世界媒体的关注,但实际上,全球被迫迁徙的收容区域广,欧洲收容的人数仅占全球被迫迁徙总人数的17%。而仅中东与北非、非洲其他地区收容的被迫迁徙者就占56%。被迫迁徙者仍然集中于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最欠发展地区。2017年,世界前六大难民收容国均为发展中国家,按收容人数依次是:土耳其,收容难民290万;巴基斯坦(140万);黎巴嫩(100万);伊朗(97.04万);乌干达(94.08万);埃塞俄比亚(79.16万)。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全球化智库(CCG)编写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
2018年7月6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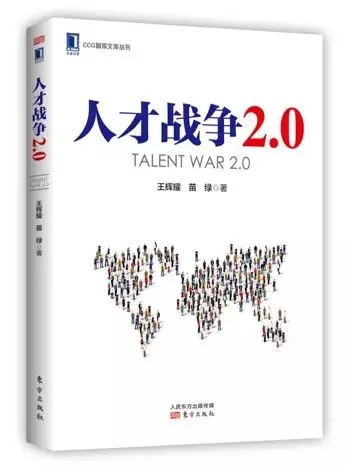
全球科技革命与人才 | CCG研究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 2017年6月2日,CCG邀请弗里德曼先生在北京总部就“科技创新重塑的全球化世界”主题发表精彩演讲,为“加速”时代中的大变革提供了乐观指南 在这个世界上,要么是“高创新”的国家,要么是“低创新”的国家;生活在世界上的人也是如此,要么是“高创新”的人,要么是“低创新”的人。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 马云是“人才”吗?
2018年6月29日 -

国际移民的区域特征 | CCG研究
摘 要 近年,国际移民 发展趋势呈现出以下特点:国际移民数量增加,所在区域相对集中,但流动性下降;经济发展刺激短期迁徙;移民流动形式多元化,尤其在大规模移民流中,迁徙的动机具有很强的混合性;被迫流离失所者规模巨大,重新安置与返乡者的比例较低,但增幅开始出现放缓迹象。主要西方国家近年反映出的政策收紧趋势并不能反映政策变化的全貌,各国根据自身发展,在移民政策变革上各有侧重。劳务移民、就业与创新,一直处于移民政策争论的中心位置。美国与英国虽然不断加高投资移民的门槛,却特别制定了吸引企业家移民的政策与规则。在移民政策“收紧”之外,新加坡为增加人口规模相对放宽移民规划,加拿大结合国际教育战略增加了高素质移民的数量。虽然中国大陆地区国际移民占总人口比重仍是世界最低,但中国也在不断从国际移民来源国,成长为治理方式与机制不断进步的国际移民目的国,外国人“来华逐梦”也呈现上升趋势。“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也成为中国规范移民的重要流向地区。 移民,从人类产生至今,一直是人类追求发展的一种既有行为中模式。20世纪之后,国际移民,则更是定义每一次科学技术革新、社会生产方式进步的特征之一。尤其在21世纪,全球化的步伐推动着商品、资本与人员的飞速跨境流动,加深了主权国家间、国家内部社会构成要素的交往方式的多元化。随之而来的,是个人、组织与国家这些全球化行为体间交往方式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势必带来交往规则的转变。尤其是以“人”为主体的跨境流动,体现了全球化中,人的生存与交往方式的变迁。规范与治理国际移民的规则,关乎促进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体福利的改进。 虽然国际移民的迁徙原因多种多样,但改善个体或是迁徙群体的生存状态,一直是人类迁徙的根本目的。移民不仅带来了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影响,也将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因素。移民来源国、目的国的不同机遇与挑战,都会不同程度地驱动人口迁徙。移民是减少贫困的强有力工具,人口迁徙的减少贫困效应,不止限于移民本身,还能为降低整个家庭和社区的贫困做出贡献。移民可以增加移民来源国的发展与投资,同时弥补东道国的劳动力缺口。移民将人口迁徙与关乎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多个关键领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中包括减少贫困、气候变化、健康、城市化、性别平等、社会保障、教育等。 国际移民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影响,总是受到媒体舆论、政治选举与各类极端思想的歪曲。因此,正确理解国际移民现象及其治理政策与机制,对全球化中人与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 国际移民现状与趋势 根据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的数据以及国际移民组织对45个国家数据的估计,截至2015年,全球的国际移民已经达到2.44亿人,占全球人口的3.3%。而在2000年和2010年国际移民的数量分别是1.73亿和2.22亿。 以2013年的数据为基础,估计全球有劳务移民约1.503亿,75%的劳务移民在高收入国家,23%在中等收入国家。只有2%在低收入国家。处于工作年龄的国际移民有2.07亿人,占国际移民数量的70%以上。高收入国家有1.123亿的劳务移民,占全球总量的75%;中等收入国家有3440万劳务移民,占23%;目的国为低收入国家的劳务移民仅占2%。 (一)国际移民的区域现状 1. 亚洲地区 亚洲有44亿人口,世界国际移民的40%都来自于本地区,有5900万亚洲人生活在非出生地的其他亚洲国家。2015年亚洲出生的移民在北美地区增长到1550万人,在欧洲地区也增长到2000万人。同时,作为国际移民的目的区域,亚洲各国共有迁入移民7508.11万人。该地区非亚洲出生移民数量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迁入亚洲的外来移民主要是欧洲人。 印度与中国两大人口大国,虽有大量移民生活在国外,但迁出移民占两国人口总量的比重仍然很小。印度是世界第一大国际移民来源国家,有超过524万印度出生人口居住在世界各地。根据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的统计与估计,中国作为世界第四大移民来源国,在不包括港澳居民与台湾同胞的情况下,有97.8万中国大陆的国际移民生活在世界各地。虽然东亚地区并非主要的传统国际移民流动区域,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与社会发展需求,包括老龄化与低生育率问题让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重新审视迁入移民政策。 为求学而形成人口流动也是东亚地区凸显的特点之一。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的差异促进东南亚次区域内的国际移民流动。在南亚与东南亚地区,人口贩运网络引发的非常规移民占国际移民的比重都很高,其中多为短期劳务移民,同时移民流中还混杂着因常年冲突与动荡局势、自然环境恶化而形成的流离失所者。 2. 欧洲地区 作为全球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区域,到2015年,欧洲已经有7614 .6万国际移民生活在该区域,过半移民(4000万)出生在本区域内,但生活于欧洲其他地区。欧洲人在本区域内的迁徙是世界第二大人口迁徙路径(第一大路径是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向北美地区的迁徙)。非欧洲出生的移民在本区域的迁徙也超过了3500万。在1990-2010年的20年里,欧洲人生活于区域外的移民数量有所下降,随后5年中虽略有回升,但到2015年仍然低于2000万人,与1990年的水平相似。在亚洲与大洋洲生活的欧洲移民数在2010-2015年间有所增加,但欧洲出生者在本区域外生活的,主要集中于北美地区。欧洲的许多国家,例如俄罗斯、乌克兰、波兰与罗马尼亚都有大量迁出移民(超过1000万)。 根据2015年的数据,在欧洲国家中,德国的外国出生人口最多,达1200万,其中主要来自波兰、土耳其、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但德国的最新数据(截止2016年12月31日)显示了德国近年的巨大变化。 图3:在德国的外籍人士按国籍所在地区分布 数据来源:德国统计局。 德国外籍人口有1003.91万。其中,国籍为欧盟国家的共有427.98万人,占在德外籍人士的42.63%;国籍为亚洲地区国家的有207.73万人,占20.69%;国籍为欧盟候选国家的有194.41万,占19.37%。2016年,在德国的外国人中数量最多的是土耳其人,达149.26万,其次是波兰人(78.3万),第三是叙利亚人(63.78万)。在德外国人数量排行前十的非欧盟国家中,除欧盟候选成员国土耳其外,只有叙利亚与阿富汗,这与2015年德国大量接收叙利亚大规模的寻求庇护者有很大的关系。在德中国人占比也随之下降到2012年之前的水平。 从英国内政部公布的各类签证签发数据看,2005-2016年,东亚地区申请入境英国的数量在2008年的短期回落后,从2009年开始持续稳步增长,成为英国迁入移民增幅最大、且最稳定的来源地区。南亚地区迁入英国的移民基数最大,但从2006年后一直持续回落,直到2014年后开始回升。东南亚地区的迁入移民虽然远低于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地区,但也一直处于缓步增长状态。 2016年申请入境英国的签证申请量与批准量排行前十的国家分别是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土耳其、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南非、泰国和菲律宾。中国公民的申请量(62.07万份)和批准量(58.19万份)均排行首位,批准率为94%。在这十大签证申请来源国中,来自沙特阿拉伯和南非的申请批准率最高,为98%。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的批准率最低,分为仅为54%和54%。签证批准率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英国对移民来源地区的偏好与其他因素的考量。 3. 美洲地区 2015年,北美地区作为传统移民迁入地区,有超过510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生活于此。迁入移民来源最多的地区分别是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2500万人)、亚洲(1550万人)以及欧洲(750万人)。相比迁入移民,本区域出生者迁往其他区域生活的人相对较少。2015年,居住于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北美出生者有130万。美国是世界拥有外国出生人口最多的国家,加拿大的外国出生人口也居世界第7。北美地区的外国出生人口有85%生活在美国,占美国总人口的14%,加拿大的外国出生人口占其总人口的20%。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2015年有近2500万移民生活于北美地区,还有460万人生活于欧洲地区。其他区域迁入的移民存量相对稳定,基本保持在300万人左右。墨西哥不但是本区域移民迁出最大国家,也是世界第二大移民来源国,2015年,有超过1250万出生于该国的人在海外生活。例如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这些中美洲国家,以及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西和秘鲁这些南美国家,在美国都有大量的移民。国内安全局势、街区暴力与跨境犯罪等问题,也导致大量本区域内国家间的人口迁徙,例如,将近100万哥伦比亚人生活在委内瑞拉。阿根廷接收的本区域外国出生人口超过200万,数量最大,这些迁入移民大多来自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墨西哥和巴西的迁入移民数量分别位居本区域国家的第二、第三和第四。但哥斯达黎加的迁入移民占总人口的比重最大(约9%)。 4. 非洲地区 非洲有超过1600万本区域出生者居住在另外一个非洲国家,还有另外1600万非洲人在其他地区生活,在非洲区域内流动的人口与迁出非洲的人口比较对称。作为国际移民的目的地,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UNDESA)的数据,2015年非洲各国共有2064.96万迁入移民,其中既包括在本区域内的国家迁往其他非洲国家的移民,也包括非洲以外区域迁入本区域的移民。本区域内的移民从2000年后开始增加,尤其在2010-2015年间增速加快。除了人口较多的国家间人口流量增加之外,国家间缔结的人口自由流动协议、破碎化的边界,以及其他造成移民与流离失所现象的各种问题,都是促成非洲人口流动加速的主要原因。非洲迁出移民最多的国家分别是埃及、摩洛哥、索马里、苏丹和阿尔及利亚。南非作为非洲最大的移民目的国,有移民310万人,占其总人口的6%。移民占总人口比重最大的5个国家分别是加蓬(16%),吉布提(13%),利比亚(12%),科特迪瓦和冈比亚(两国同为10%)。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全球化智库(CCG)编写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
2018年6月26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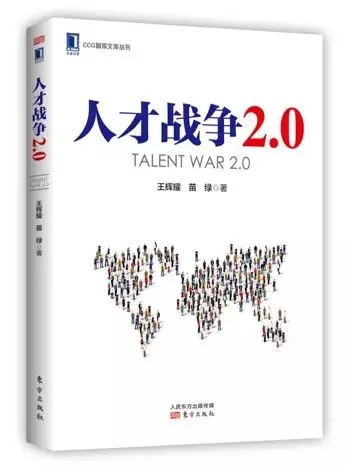
CCG研究 | 人口、人才流动与经济增长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 人口流动是非常正面的事情,对此大家需要有正确认知。流动对发展至关重要,虽然全球的媒体报道并不见得看到流动的正面影响。但我们应该去看到流动的贡献,应该去改进公众的认识,应该去协助流动来促进发展 。 国际移民组织(IOM)主任———Ovais Sarmad 人口数据与经济数据的历史性变化显示出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700年,世界上有20%的人口居住在西方,1913年这一比例上升至33%,到2003年下降至17%,联合国预计到2050年将下降至12%——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发达国家生育率急剧下降。 1800年,世界上32%的GDP产生在西方国家,到1950年这一数字上升至68%,到2003年下降至47%,到2050年预计西方国家占世界GDP总量的比例将小于30%。这显示出经济力量不再集中于西方国家,而是开始了在全球范围的分布。 反观历史上五次国际产业转移大潮更是加速了经济力量的发散分布,这背后的动力是成本更廉价。 第一次浪潮: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从英国向欧洲大陆和美国转移,使美国在19世纪末跃升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强国。 第二次浪潮:二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从美国向日本和原联邦德国转移。德国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日本建成了第三个“世界工厂”。 第三次浪潮:20世纪70~80年代,从日本转移至东亚地区,催生了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奇迹。 第四次浪潮:20世纪90年代至2012年,美国、欧洲、日本、“亚洲四小龙”都向中国转移产业尤其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此让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第五次浪潮:2012年至今,中国的低端产业向东南亚、非洲相关国家转移,高端产业则向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回流。 在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承接地的成本廉价是重要的因素,其中劳动力成本又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最近一次国际产业转移中,中国是主要转出地,背后现实是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非洲则是重要的承接地之一 :2015年中期人口数量约11.5亿,每年增长约3000万——这些人大量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年轻人比例高,工资水平是我国的10%~50%,而且展望未来20年,由于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工资长期难以上涨。 这正是人口因素赋予欠发达发展中国家的机遇,抓住了就有机会成长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例如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等国。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得益于两个重大因素:人才聚集和智能工厂、工业机器人的应用。 这两种类型的产业转移(劳动密集型和高端制造业)将带来何种人才流动模式呢?最明显的就是从产业输出国向接收国转移高端管理者和工程师等人才,以及从产业接收国向输出国输送接受培训后再回归的人才。 除伴随着产业转移带动人口流动促进经济增长之外,发展中国家由于内部产业和经济规模提供的就业机会不足,也促使人们离开家乡,走出国门寻求发展。同期,发达国家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有获取外来移民以进行补充的需求。这种流动又会对经济产生如何影响呢? 以美国中西部“铁锈地带”的城市为例,巴尔的摩、匹兹堡、费城、克利夫兰、圣路易斯、底特律、代顿等,其中底特律曾是美国第四大城市和制造业中心,但2000~2010年随着汽车工业迁出,1/4的人口流失,大大降低了城市的财政水平,也导致投资不足和公共服务减少;其他城市也经历了类似的产业空心化历程。为了振兴经济,俄亥俄州的代顿市已接收了很多来自土耳其的移民家庭以促使当地经济恢复。 在德国,小城戈斯拉尔拥有约5万人口,其市长宣布允许难民从周边城市哥廷根和布伦瑞克来此定居,以弥补人口减少和劳动力短缺——已严重阻碍了当地以高端温泉为主的经济发展。 在我国的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文莱和马来西亚,有一大批外籍女性家务工作者,她们主要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据估算在亚洲的人数已超过200万。 对于移民输出国家来说,来自海外侨民社区的国际汇款、投资、人力资源、技术与专业知识等能够加速其来源国城市的发展。例如,摩洛哥的侨民群体在他们的家乡城市投资了房地产和其他生意;2013年,墨西哥侨民与移民事务部设立了Maghir Bank,进一步增强本国与海外侨民的金融联系;在埃及,2011年政治危机导致外汇收入骤减,海外侨民群体向埃及发展基金增加汇款和捐赠,部分地缓解了状况;在我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发展初期,福建、江苏、浙江、广东等东南省份从侨汇和侨胞投资中获益良多。 由此可见,管理得当的话,人口流动对输出国和输入国均会带来经济增长,实现双赢的局面。 今天的世界虽然遭遇到种种“逆全球化”现象的冲击,但全球化发展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同样,人口流动也是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2014年,全球超过5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有预测称,到2050年这一数据将达到64亿。发达城市的移民人口飞速发展。 全世界近五分之一的外国出生人口居住在全球主要的发达城市。世界大都市纽约、伦敦、悉尼的移民人数超过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迪拜、布鲁塞尔的移民人数已经是当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即使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城市也正在成为移民的流向地。 这种流动,有助于带动不发达地区发展起来,分享人类进步的成果。 全世界近五分之一的外国出生人口居住在全球主要的发达城市。世界大都市纽约、伦敦、悉尼的移民人数超过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迪拜、布鲁塞尔的移民人数已经是当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人才战争 2.0》, 王辉耀、苗绿著,东方出版社。
2018年6月21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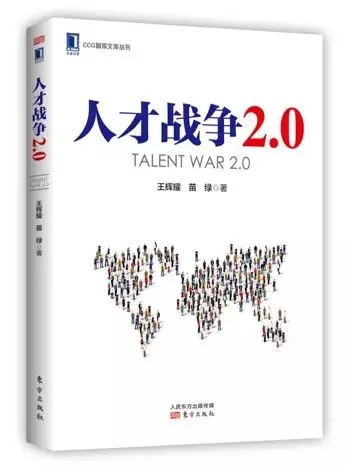
人口危机:年轻人都在哪儿 | CCG研究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
2018年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