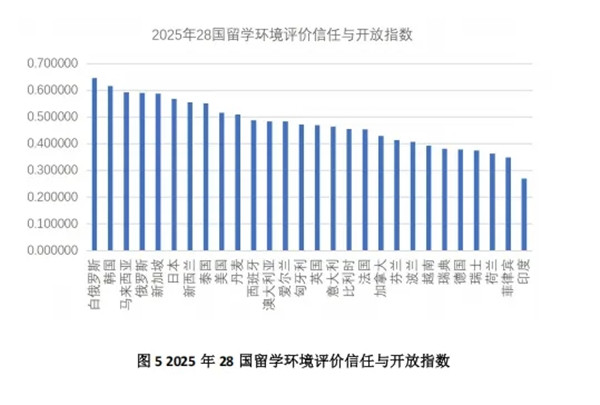【搜狐教育】苗绿:中国人拿诺奖“推手”功不可没
2015年11月4日
主持人:屠呦呦获得诺奖是否说明我们的人才培养机制,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个突破?
苗绿:对的,无论如何是一个中国的科学家获得了诺奖和世界的认可。有人说我们有中第三世界心态,总是对国际的承认很敏感,但总之国际标准认可了中国人,而屠呦呦一定是符合这样的标准的。
屠呦呦女士得奖我觉得是一个必然也是一个偶然。当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教育体制不断的改革,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时,社会就会出现这种人才。同时我觉得有一定的偶然性。无论屠呦呦得奖还是莫言得奖,其实中间都有“推手”:屠呦呦得奖不能不提饶毅教授在国际上的力荐和传播,莫言获诺奖也少不了葛浩文、陈安娜这样的“功臣”。
其实这说明了要获得诺奖这样的国际大奖的承认,中国人缺乏一点国际经验或国际途径,需要中间有国际的转化如国际语言、人类普世的语言帮他们表达,未来中国想要获得更多的这种国际大奖少不了这种国际转化。
我特别同意刚才谢维和教授讲的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国际交往非常重要。今天英语可能只是一个工具,这背后其实是一套思维方式。为什么我们老说印度人培养了很多世界500强的CEO,而中国没有,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背后的思维逻辑,他们懂得这套国际语言国际体系和它的思维方式。可能我这样说有点功利性的感觉,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如果说缺乏这个环节很大程度上就限制了中国的人才培养和走向国际。
主持人:中国的科研和教育如何才能国际化,怎么才能更好的国际化?
苗绿:我觉得是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比如说现在提倡到中国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我觉得中国教育同样是这样的。今天中国人在国外重要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很多,但真正引用率却很低,我想这背后跟中国的实用主义哲学观有关系。中国的教育国际化也提了很多年,我们的智库这些年也一直在做留学蓝皮书,有一个数据是现在海外有108万中国留学生,但海外到中国的留学生只有30多万,而且其中一半都学语言的,获得学位的非常少。
2003年到2014年,过去十年持有F1签证在美国的高中中国籍学生增长60多倍,这个数据还是很惊人的,而且留学低龄化比较明显,而且读本科的数量也很多,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中国人是重视国际教育而且是有需求的,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在推动中国教育的发展,留住这样的生源?比如我们可以发展中外合作办学,像宁波诺丁汉、上海纽约大学等等这样的学校可以更多的在中国遍地开花,可以留住一部分的孩子,把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提升。
还有比如各大个城市高中都有国际班,我们可以把这种经验更多地推广,还有中国的高校也可以走出去,与别人进行合作。一方面引进来,一方面走出去,来推动中国的高等教育或者中国教育的国际化程度。
主持人:像日本、以色列这些年获得诺奖的人很多,这和一个国家的教育有关系吗?
苗绿:肯定是有关系的,像一个文学奖的得主,他跟自己国家的文明、文化有密切的深厚的关系。当然教育分成很多种,可以是学校的正规教育,也可以是社会的教育,整个文化的滋养。有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好象接受的教育并不是很完整,或许没有正规的受到完整的基础教育或高等教育。
因为我是北师大出来的,因为在师大有一个作家班是和中国作协一起联办的,所以他也是我的师兄,也是校友,跟莫言老师接触算比较多,也比较了解莫言老师。他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他在社会上和军队里很多年,这种社会教育对他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其实屠呦呦和莫言两位大师很大程度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我前面提到的他们都有国际传播或推广的过程。莫言老师在得奖之前已经受到国际承认了,在得诺贝尔奖之前,意大利、美国等给他颁了很多奖,有时候跟他开玩笑说拿奖拿到手软了。莫言的作品很受西方读者的喜爱,他有一些马尔克斯的现实主义手法的影子,他的作品很大程度上西方读者能看得懂。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莫言得奖我觉得跟国际化有一定的关系。
主持人:您认为我们的人才培养机制该如何改革?
苗绿:人才机制分为培养、引进、使用、激励各个方面,我觉得这些年我们国家在国际化程度上面有非常大的突破,包括中国推出的“千人计划”确实为中国的人才使用生态开了一个口,更多的使用国际化人才,更多的信任,然后吸引他们回到中国。虽然今天讨论的重点是培养人才,但是有时候是土壤问题。我个人还是提倡中国未来教育发展需要更多的引进国际化元素。改革开放刚开始引进来很重要,但开放促改革,这未尝不是一种方法。这也是中国人才培养机制改革的一种途径。而且我始终认为最终咱们的目的是要培养像文艺复兴式的人物,目的性不能太强,哪怕你是经济学家、科学家,我们需要的是去发现一个事物带来的乐趣,创新和创造本身带来的价值,而不是说我做了一个事要去拿诺贝尔奖,目的性太明确可能最终培养不出最优秀的人。
本文选自搜狐教育,2015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