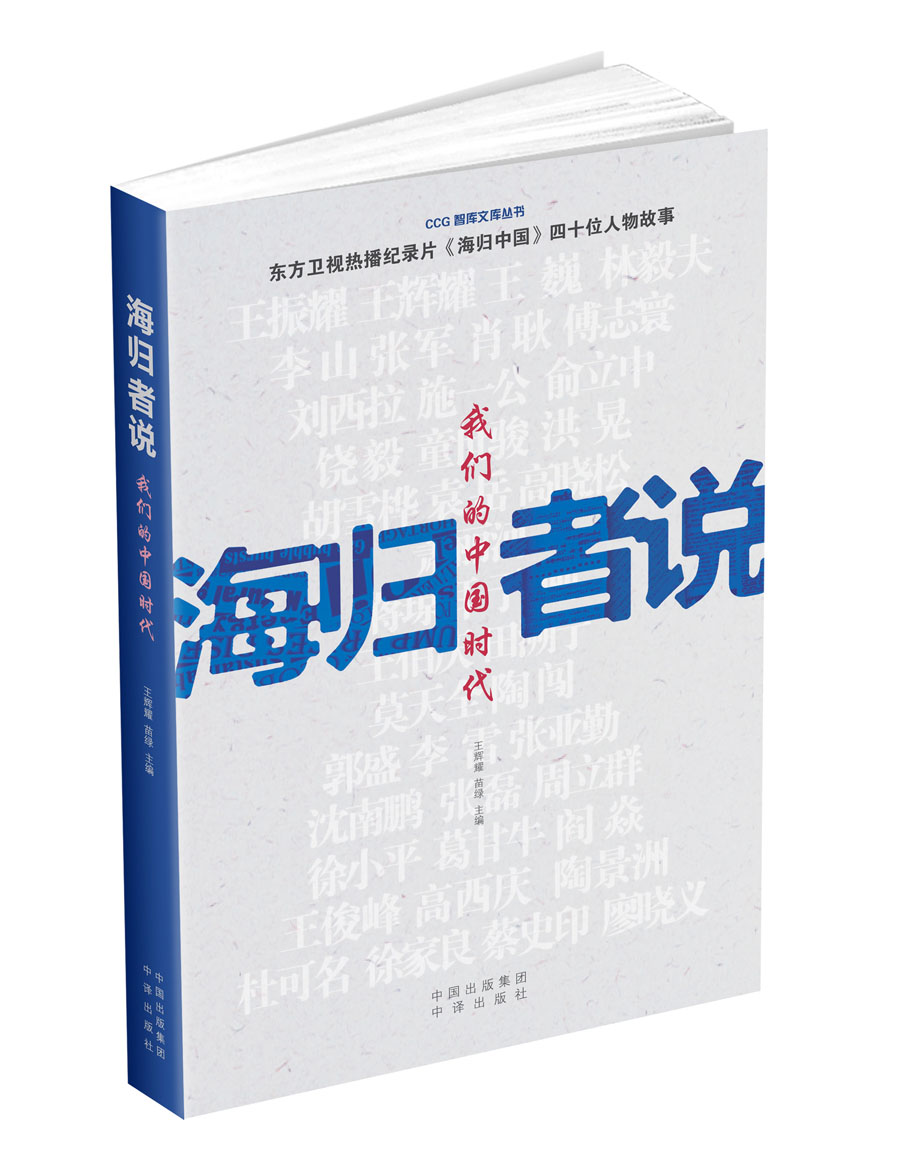陶景洲:由“误会”开始的人生 | 理事风采
2016年2月22日
▼
我上大学是一场“误会”,读法律是一场历史误会,当律师也是一场历史误会。
我本来应该下乡两年,而父母非要我考学。当时可以报三个志愿,我报了北京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后来,我妈妈偷偷到县教育局把我的第一志愿改成了安徽大学。之后某天我到教育局长家玩,他跟我提起说我妈把我的志愿给改了。我说:“不行,这是我的志愿,我要再改回来。”于是,我改回来,上了北京大学。
我当时报的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接到通知却变成了北京大学政治法律系。政治法律系听都没听过,到了学校才知道,法律系是绝密专业,必须根正苗红才能读。
大学毕业后,我父母想让我回安徽,我却要考研究生。当时有出国预备研究生和在国内读的研究生。我觉得出国研究生可能比较难一点,就考了出国研究生。
我是1982年7月14日到巴黎,到了就被派到外地学了一个多月的法语。加上出国之前培训的三四个月,总共也不到六个月,进了大学很多课都听不懂。
当时,我买了一个收音机和一个磁带机,把法国电台里的法语节目录下来,反复听,听不懂的就去找同学帮我听一下。那时我也得到了贵人相助,一个传教士总希望我能够信基督教,一天到晚来跟我说话。我就听他说,而且他每次都会给我讲解法语,分析怎么断句之类的,帮助我提高了语言。还有就是扎在法国学生堆里,一天到晚跟着他们,听他们说话。可能他们一个晚上都在说话,而我一句话也插不上,但不停地练习自己的听力,也是一个提高法语的方法。
后来为了留下继续学业,我决定自己想办法赚钱。我去找了一个对我特别好、退了休的教授,跟他说了我的想法,说我想找工作。他答应帮忙。我就说了两个律师事务所的名字,有一个他比较熟。于是,我就进了这个事务所实习。实习之后,我就爱上了律师这个行业,对原来学的行政法也不那么感兴趣了。因为行政法的具体实用价值太低,而律师相对来说实用价值更高一点,所以我就毅然转行到商法这个领域。
在事务所实习,接触的都是商法,我就自学了很多关于法国商法、公司法、民法的一些东西。做律师,一开始是生活所迫,之后则是自己的选择。这么多年来,许多地方曾经让我做这事那事,但我觉得我只会做律师。
与意大利时装界巨子贝纳通合作,帮助他们进入中国市场,是一个巧合。当时他们到我所在法国的事务所商谈他们在法国的投资,我就认识了他们。他们对中国很感兴趣,想到中国投资,问我能不能帮忙联系。我答应后,他们就让我先去威尼斯见他们的总裁,说服他到中国投资。见过总裁之后,我就回来安排他们到中国做生意的事情。
当时,中国零售行业是不开放的,只允许外国在中国生产,不允许在国内销售。所以,要进口服装在中国卖几乎不可能。最早我们帮贝纳通联系驻华外交人员服务部,这是一个免税机构,只允许外交官和驻华外国人进去购物。我们就和中国免税品公司合作,让他们接受贝纳通的服装进店销售。
中国的零售业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才逐步放开,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国在经济上采取了更加开放的模式推动发展;二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造成苏联政治上的不稳定,降低了投资者对它的投资兴趣。
1991年初,我觉得到了应该回国发展的时候,因为柏林墙倒塌证明了未来的资金应该会流向像中国这样经济上开放的国家。
我出去时就觉得出去是为了回来,是为了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1991年,我回到中国,回来时的正式身份是一家美国保险公司的首席代表。因为当时中国在律师事务所这一块是不开放的。直到1992年5月,中国司法部和国家工商总局才出了一个规定,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开业。
1991年,我回来时加入的高特在中国的办公室一共四个人,发展到最后,有六十多个人,都是我的团队。
当时回国也有个人发展方面的考虑。我们主要是代表外国公司到中国来投资,如果我人在巴黎,对方要带我来中国谈判,就需要考虑成本问题,因为他要付我机票和酒店的费用。而如果我在北京,他们就没有这些开支了,只需要支付我的时间成本,我就能更容易介入到一些项目的谈判过程中。而且,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事务所很少,大家也刚刚开始了解中国,所以,不经意就可能会见到世界上最大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而如果在巴黎,可能永远见不到他们。到中国来,他们会找我们这些年轻律师直接谈一些问题,接触就会更多一点。另外,回来以后,一些世界上的政要到中国访问,可能都会和我们见面,但在当地,既见不到总理也见不到总统,回来以后比较容易见到这些高级官员。
回国后我接手的第一个比较有名的案子是麦当劳在中国北京饭店附近建的第一家店。这家店不是麦当劳自己所有,是与北京市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合资的项目,因为当时国内要求必须合资。
我们的工作是负责起草合同。因为有中国企业参加合资,而且麦当劳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品牌,中国政府很重视,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个项目没建两年就出现了重大问题。建店之后,李嘉诚把这家店所在的那块地买了下来,让麦当劳搬走。我们主要处理该不该搬家,搬家应该给什么补偿的问题。
麦当劳是一个符号,只有在消费水平逐步上升,而且人们的生活节奏变快时,麦当劳才会进来。麦当劳进来时中国并不是那么开放,但这肯定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中国在开放的道路上继续往前推进。
开放,需要技术上的革命。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遭遇了很多失败。造成这些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很多企业还没有学会走就想跑,有些企业是想一口吃个胖子,而有些企业则把走出去作为政绩。这些都是错误的指标。企业在决定走出去之前,要仔细衡量走出去的方方面面,要算一本经济帐,而不是说为了,在报纸上宣传一通,或者是国营企业老板会因为这个合同升一级,就盲目的想做大。
二是缺少管理国际跨国公司的人才。很多土生土长的企业领导者可能还无法管理一个跨国公司、一家跨文化的企业。他们虽然了解在中国的办事风格,却并不一定了解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做法,有时候按照中国的办事方法去做国际上的事肯定要失败。另外,出国留学的一些海归也是半瓶子醋,在国外可能待了一年镀了一层金,就算出国留学回来了,但这个金镀得不够水平,随意擦一下就掉了,经不起风吹浪打。要把管理企业的担子交给他们,也有一定风险。
海归是中国和世界之间的桥梁,他们无形中帮助中国和世界建立了一个高速公路。如果没有留学生,中国与世界可能就像两座高山之间没有桥一样,需要绕很弯的路,浪费很多人力物力。现在,我希望通过海归们能够发展起来。也希望社会能给他们一个特别发挥想象的空间,让他们自由地去发明、发现和创造,并能多容忍他们有特别多的失败。只有这样才能够发展起来一些新的技术革命。
文章选自《海归者说-我们的中国时代》,主编:王辉耀/苗绿,中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