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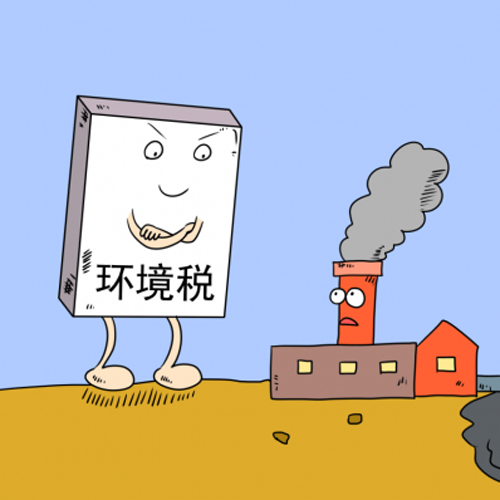
【中国科学报】环境税能否破解污染难题?
去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已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按照“税负平移”原则将现行排污费改为环境税。环境税将于2018年1月1日开征。这也意味着,目前环境税已进入最后立法阶段。 从排污费改为环境税意味着什么?又会带来些什么?听听两会代表、委员们怎么说。访谈嘉宾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张连起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环境保护局原总工程师包景岭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青 将更加规范有效 《中国科学报》:用环境税替代排污费等各种已有环境税负是否为治理污染的最终解药? 吴青:环境税只是其中的一个手段,并不是唯一的,环境治理需要多种措施,包括环境立法、环境政策和行政执法监管等。 张连起:要应对当前严峻环境态势,根本上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环境治理手段,当然,环境税是保护环境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手段,也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一个政策工具,对环境治理、向污染宣战是非常有效的。 建立专项转移支付制度,通过费改税,将税收统一上缴中央财政,由其统筹分配,拿出一定比例以专款专用的方式反哺地方。此外,除了从污染源头查处、防治外,还应建立跨地区的联防联控机制,让环境污染防治更有成效、更符合科学规律。《中国科学报》:环境税与以前的各种排污费有何不同? 张连起:排污费征收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形式上是一种行政收费,而且这种方式偏重筹资和排污末端治理,忽视了诱导机制的运用。 排污费是地方收费,没有环境税的强制性那么强,地方政府选择性收费也存在不公平的可能性,这种方式还存在征收程度不规范、征管法规强制性不足无法有效震慑违法行为、环保部门执法力度不足难以依法足额征收、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造成征收不到位等问题。 包景岭:环境税是一个很好的策略,相当于统一了标准。统一标准有利于统一管理。过去收费收了很多年,是各个省市按国家环保部很多年前统一制定的一个标准收,各个地区按此标准收费以后发现了一些问题,有的做了一些调整,这带来了一些差异。我们曾经做过一些统计,比如北京、天津和其他一些典型地区的收费标准,平均下来大概有这样一个比例,即9:7:1,用其他典型地区做1的话,天津收费是7倍,北京是9倍。环境经济红利 《中国科学报》:会带来怎样的环境和经济红利? 张连起:环境税实施之后,减排力度肯定会加大,这是毫无疑问的。设计方案的杠杆作用大、执行力大。 特别是大多数企业都有环保设备,原来因为电费比较高,就不开减排设备,但实施环境税之后,如果不开设备,税比较高,它就会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对排放有抑制和降低作用。 排污费由环保部门征收,专款专用,而环境税由税务部门征收,可以统筹使用,甚至全国的环境税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统筹使用,比如京津冀的大气污染,可以联防联控。 环境税应该到了最后立法阶段,会促使排污企业通过技术改造、设备与投资或充分利用现有的环保措施改善环境。 包景岭:会促进治理,过去有些地区收排污费比较少,大家治理环境积极性不高,除非有强烈的行政命令,现在通过调整税和费的关系,会出现有些企业达标了也要进一步治理的情况,因为税是按排放当量计算的。只要税非常合理,就会进一步提高企业治理的积极性。 吴青:环境税是费改税,是在原来排污费的基础上改成环境税的,其最大的好处是将政府收费变为了法定的税收。不交费或少交费并不涉及法律责任,但不交税或少交税就涉及法律责任了。 《中国科学报》:如何避免买了排污权,污染不降反升的情况发生? 张连起:税的刚性与排污费不一样,对污染的抑制作用至少比排污费好得多,当然,现在环境的压力承载力是多方面的,在相当范围内是综合施策。 包景岭:环境税需要与其他环保法诸如《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统一,超标的地方一定要与其他惩处措施有机结合起来。 吴青:排污权只是解决企业排放总量指标问题,并不能解决企业是不是达标排放问题。所以,企业即使买了排污权,也还是要加强对排放的监管,包括达标排放,包括减低排放总量。应进一步测算、分析和完善 《中国科学报》:有了税就不再收费了吗? 张连起:应该是取代费,各种费就没有了,从目前的几个意见看,环境税锁定的范围也不是所有排放,是不是完全取消所有费用,尚未完全确定。但改为税是大势所趋,水到渠成。如果企业排放少,自然要交的环境税少,是环境激励措施。开征环境税,肯定不是国家为了多征税,而是抑制污染排放。 包景岭:环境税是统一到一个底线,理论上达标了,其他的费用就没有了,但对特殊地区,要有新的计算方法,避免重复征税。这只针对正常达标排放的企业,对超标排放的有别的法律来管理。《中国科学报》:如何避免增加企业负担? 包景岭:长期以来我国收的排污费用是低于治理成本的,当然中间也做了一些调整。例如,环境税的实施确实会促使一些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关停,同时让清洁生产企业减负。文章选自《中国科学报》,2017年3月16日
2017年3月21日 -
朱锋:东亚政治开启“新三国演义”
专家简介朱锋,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面对着困扰北京、东京、首尔三边互动架构的诸多消极因素,中日韩关系究竟应该怎么处?这不仅是一个争议性的政策问题,更是摆在东亚政治面前的世纪难题。当前中日韩关系的低潮并非偶然。 19世纪末以来,中日韩从未出现过同时强大和繁荣的局面,东亚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出现陆、海分离的地缘政治结构开始被打破的现实,而观念与制度层面更是前所未有的分裂。再加上美国因素的牵引与干扰,中日韩关系的“新三国演义”充斥争议和对立实属正常。 这是东亚地缘战略结构从未有过的新变化,稳定和改善中日韩三国关系也必定绝非易事。单纯从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入手,或者单方面的克制和忍让,恐怕都难以打开中日韩三边关系的新局面。从这个角度,笔者对笪志刚先生《环球时报》2月22日见报的《中日韩破局不能坐等域外国》一文存有异议。安全关切先于经济利益 国家间的经贸关系并非只是单纯的经济和贸易安排,背后的外交和战略考虑常常是决定经贸政策选择的关键因素。安倍政府在2013年下定决心加入奥巴马政府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PP),首先考虑的不是日本的贸易和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十足的政治和战略决定。 TPP的本质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杠杆,其目的是通过建立排斥中国的地区性贸易集团加强“孤立中国”的地缘战略集团。安倍力压国内一度强大的反TPP势力,愿意向美国开放汽车、农产品市场,就是为了全面增强美日军事同盟,避免美国在未来可能的日中军事冲突中战略犹豫。 韩国在2016年7月做出“萨德”部署决定,最根本的原因同样是——韩国必须在朝鲜导弹与核武器威胁面前,强化韩美军事同盟作为韩国安全的可靠保障。这是1992年中韩关系正常化以来,韩国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战略“再选择”。面对来自金正恩政权迅速的核力量和导弹发展,韩国把国家安全的“宝”彻底押在美国身上。 近年来,中日韩之间出现的这种扩大的安全对立,有着深层的亚太地区战略性和结构性根源。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和安全是相互关联、但又彼此分离的两个领域。经济上的利益计算和相互依赖带来的红利,并不能必然取代和削弱安全问题的关注。 安全利益的评估和选择,对一个国家而言一定是优先于经贸利益的“高位政治”,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法则。经贸关系无法替代安全利益的估算,同样也是国际关系冷冰冰的现实。现阶段重在安全“止损” 然而,中日韩关系必须改善,当代版的东亚“新三国演义”已不会重复历史版的“联吴伐魏”或者“兴兵灭蜀”!“新三国演义”的基调和目标必须是三国共存共荣,致力于一个崛起的亚洲,着眼于一个团结和联合的亚洲,打造中日韩三国人民共享福祉的稳定局面。这就是中国领导人所提出的“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愿景。 为此,打开三国合作的钥匙不仅是经济的,更需要政治、外交、安全和战略的。但这必然是一个艰难的历史进程。其手段不仅在于实力对比的新变化,更是在于三国的成长与成熟,在于三国之间是否能够重建理解和尊重。 当中国的游客一到节假日就挤满韩国的明洞和日本的新宿,当中国赴日留学生远远多于日本赴华留学生,一个开始身强力壮的中国,“心”需要同样的宽大和壮实。上演好东亚“新三国演义”,中国人一定要有自信、宽容和坚定的战略意志,韩国人和日本人面对中国再度崛起的历史性趋势,则需要有同样的包容、理解和敬畏。 改善中日韩三国间的关系,不是简单地思考“经济出路”或者贸易变量,也不能奢望三国间的民族主义冲突能迅速平息,“历史问题”和领土争议的解决更是路途遥远。稳定和改善中日韩关系需要对三国深化的“安全困境”做出客观、全面和准确的判断和整体性的战略思考,无需一味指责对方,也不必用过度的恐惧或者仇视的心态看待彼此。 我们首先需要有足够的心理和战略准备,中日韩关系的改善进程很可能是缓慢、长期的。着眼于现有中日韩业已建立起的广泛与深入的经济社会联系,给中日韩争议和摩擦“止损”非常重要。 具体来说,就是要避免关系持续对立与恶化,避免出现直接的军事冲突,避免安全争议扩展到国家间关系的基础性领域,例如经贸和社会性交往尤为重要。而“止损”的关键,就是要在三边关系的各种冲突点上,建立和开展起双边事务性和功能性磋商,通过设定行为规则、培养信赖措施,以及增强彼此务实合作,有效管控冲突性议题上的潜在危机。在斗争中寻求破局 中日韩三国关系的改善离不开“斗争”,需要我们有决心表达和反映“中国关注”,在斗争中寻找“破局”的方式和途径。 在这方面,中韩与中日又有所不同。韩国虽一意孤行部署“萨德”系统,严重损害中国的战略利益和东北亚的战略稳定,但中韩之间的政治沟通仍然好于中日。中韩之间的安全对立,也远未像安倍政府的日本那样一心以“制衡中国”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尽管朝鲜问题确实是卡在中韩间的一道“坎”。 对于日韩无视中国战略关注、损及中国安全利益的行动,我们将坚决斗争到底。但斗争毕竟是手段,合作共赢才是目的。 中日韩三国关系的改善,更需要我们有坚定的“战略耐心”。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缘战略形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复杂和微妙。一方面,中日韩的经济社会联系前所未有地深化。2016年中国赴日游客数量增长28%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坚持中日韩经贸与投资合作,共同推动包括三边自贸区在内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是我们塑造亚洲繁荣与和平的基本信念。 但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来中日韩之间安全利益的纠葛和对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严峻。在安全关切上相互“靠拢”,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找准方向、坚持不懈。三国的社会和媒体更需要担任起沟通的桥梁作用,为彼此的客观和理性认识注入正能量。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7年3月20日
2017年3月21日 -
王缉思:美国出了什么问题?
不管怎么说,最后特朗普当选利用的是美国白人工薪阶层对于移民的恐惧和对于过去逝去时代的文化怀旧。专家简介王缉思,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一、奥巴马八年政绩评估 美国出了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大家对奥巴马八年不满意?当然也不是所有人不满意,至少给特朗普投票的人觉得应该有一个“更好的美国”。 事实上八年前,奥巴马说上台后要带来变化。那时正好是三十年代以后最严重的一场金融危机,同时小布什又打了两场战争,极大地消耗了国力,美国形象也很受损伤。当时我引用了美国很流行的一句话形容那时候的美国——“没有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八年过去了,支持特朗普的人也这么说。八年前60%的人认为美国没有走在正确道路上,今天还有60%的人认为美国没有走在正确道路上,我猜想再过四年或者八年做调查还是一样的:美国没有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反正美国人民总不满意,也很难让多数美国人民满意。 其实奥巴马八年做了很多事情。一个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改变了财政状况,财政赤字削减不少;然后又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八年前奥巴马说“再工业化”,让制造业回归,还有一个出口倍增计划;现在特朗普也说要让制造业回归。奥巴马还依靠当时民主党在国会的多数席位,推行了全民医保;能源方面,民主党一贯的政策和奥巴马本人的想法,都把气候变化看作很重要的议题——美国应该开发新能源,不要依靠传统的石油资源;于是开发了页岩油、页岩气,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大大减少了能源进口,甚至有能力出口能源了。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法律规定不能出口能源,我们要看看这个法律会不会修改。奥巴马还改革了《移民法》,对移民相对比较宽松。 奥巴马说我这八年是“内政优先”,现在特朗普也是说“美国第一”。我先做一个断语:他们两个人的政策设想并不是完全相反的。奥巴马还说要“不做蠢事”,实际上是指小布什时代打了阿富汗、又打了伊拉克,花了几万亿美元,耗费极大国力也没有解决问题。我跟我的朋友写了一篇文章,说美国进入了“韬光养晦”的时代,外面的事少管,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外面事干的是什么?一上来就搞“巧实力”,搞外交公关,改善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重返经济优先的原则——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大家比较熟悉,他做了一些事。 奥巴马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这八年没打仗。这是我有点吃惊的地方,八年以前我想,奥巴马一定会打仗,因为前任没有一个不打仗,美国人几十年来永远在世界上打仗。居然八年没有打一场像样的战争。美国参加过利比亚战争(2011年),但这主要是欧洲人打的,美国人出动的军队,一架飞机没掉,一个人没死,花了几十亿美元就解决了问题。有人曾经出主意说要打伊朗,他不打;有人出主意甚至已经准备动手就是打叙利亚的政府军,他也没出手。所以说奥巴马使用武力很谨慎。不过无人机打死了恐怖分子,也伤害了不少平民。本·拉登是奥巴马在任时处死的。 军事方面,奥巴马有一件事情没有被广泛报道——开了“网络战”的先河。美国人觉得伊朗核武器对美国的危险太大了,于是通过网络,把伊朗发展核设施的电脑系统给破坏了。这是跟以色列人一起偷偷干的,伊朗吃了哑巴亏。以色列还当然搞了一些针对伊朗的暗杀活动。 同时,美国缩减了军事预算,调整了军事战略,在全球治理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问题)上比较积极。 最后,关于“亚太再平衡”,奥巴马光说不练,没有多少实际行动。 我对于奥巴马的总体评估是——经济复苏了,而且好于其他国家;失业率下降了,现在的失业率是经济危机以来最低的,4.6%左右或者更低;外交上,对于美国来说是得大于失;开发了很多新技术,对就业造成威胁——这点很重要,美国人现在很不满意,有些人说我失业是因为机器人和很多新技术代替了人工。 这几年奥巴马干得不好的地方也有很多。有些不是政策上的问题,而是长期以来美国增加了贫困人口,中产阶级财产缩水了。有统计说明,从1996年到现在,中产阶级的平均收入还是在6万—9万美元左右(一个家庭)。工资性收入占财富比重是下降的。同时左翼跟右翼(共和党、民主党及其他所谓的“茶党”)政治激化日益严重。有一次我访问美国,正赶上他们的债务危机导致政府关门。结果2013年10月初,政府机关真的就关门了。这是债务危机和两党之争造成的。比这个稍微早一点的是“占领华尔街”运动,说美国有99%是穷人,1%是富人。靠左的人主张要加强金融监管,靠右的人发起了“茶党运动”。茶党就是现在支持特朗普比较多的人群,他们在“占领华尔街”运动时期实际上就已经出现了,以白人、老人、男性居多;南方特别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茶党比较多。 这样一看,奥巴马八年来有很多令人不满意的事情,为特朗普当选埋下了伏笔。二、从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看美国面临的严重挑战 特朗普初选的时候就出人意料地战胜了诸多对手。而且他本来也不是真正的共和党人,却一路胜出,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这个房地产大亨、政治新手在各方面打破了传统。过去我们经常说美国是金钱政治,是靠钱来支撑的。今年看不出这种情况,因为特朗普本来就有钱。他没有花什么钱在电视上做广告,因为他本来就是干脱口秀等各种事情的,上电视本身就是广告,就是收入。这是一场依靠“特朗普”品牌和一个简单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就赢得的选举。这个人在美国政治精英中支持率是很低的,在共和党中一开始是孤立无援的。 我2016年去了两次美国,有各种各样的交流情况,一谈起特朗普,我的朋友(我的民主党、共和党都有)都说:“这样的人怎么能选上总统?”一个比较左的民主党人在选举前两三个月跟我说:“太悲哀了,居然有40%的美国人支持这样一个蠢货!”当时他完全否定特朗普有当选的可能性,但他仍然感到美国出了大问题。还有一个有名的国际政治学家叫约瑟夫·奈(他发明了“软实力”这个词)在特朗普当选前十几天到北大做讲座,私下跟我们说,没法想象这样的人居然能够去竞选总统。约瑟夫·奈的观点是美国不会衰落,下一个世纪还是美国的世纪。但那时他的思想开始有点动摇,觉得美国这个情况使人感到忧虑,但还是认为特朗普不会当选。 最后特朗普当选了。有人说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我们中国人一般对只要是发生过的事情,有一种思维的习惯,就认为历史必然是这个样子的,说“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我本人不承认说是“必然”,还是有某些偶然性。我个人犯了判断上的错误。我以为希拉里会当选,原因是我观察美国那么多年,凭着经验,认为媒体还有民调基本上是准确的——90%以上的媒体都认为希拉里会当选,而且会以比较大的比例当选。那还有多少疑问?我就相信媒体吧。 但媒体失算了,民调也失算了。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包括技术原因,当然也包括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技术问题。比如民调的时候都会打电话或者通过E—mail等去了解大家到底支持谁,但忽视了可能有20%、30%的人拒绝表态或拒绝参加调查。这些人支持特朗普的多一点。为什么?因为支持特朗普的还有很多精英、大学生们,他们知道多数社会精英都觉得特朗普这个人这么差劲,知识浅薄,话都说不清楚,语法错误连篇,这样的人如果表示我支持,就显得我很弱智,所以民调时他们不说话,结果到最后偷偷地给特朗普投票——你们都觉得他不行,我就是喜欢他! 我的错误在于相信媒体,以为佛罗里达州、宾夕法尼亚州等等“摇摆州”,肯定是民主党的,但后来摇摆州的多数都摇到特朗普那里去了。所以,隐藏的选民最后把希拉里给推下去了。 一般人去调查,总是去大城市、有点知识人的里头调查。但受教育比较少的人、乡镇选民投特朗普票的特别多,也有人干脆不投票。事后我看有文章说,媒体到黑人选民那儿调查,问为什么不投希拉里的票,黑人说八年前投了奥巴马的票,四年前也是投了奥巴马的票,觉得奥巴马上来以后应该对黑人好一点吧,结果没有见到黑人待遇改善,我还要继续他所支持的希拉里·克林顿的票吗?不投了,谁也不愿意支持。还有些人投特朗普的票是因对希拉里不满意,因为他们对现在的政治形势不满意。但特朗普坚定的支持者里,有很多人觉得他会改变美国的面貌。老实讲,我认为四年以后美国面貌不会有多大改变,那些中产阶级、蓝领、白领在四年以后的收入会增加很多?境遇有很大改善?我非常怀疑。也就是说经济可能是好转的,但好转的结果也许仍然是华尔街的“肥猫”和特朗普这样的房地产大亨把钱拿回去了。这是我个人的判断,未必正确。 政治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所谓“十月惊奇”——十月爆出的邮件门事件。为首的人是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还有中央情报局等等,这些司法部门、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白人居绝大多数。这些人大概支持特朗普的人更多一点,所以把这个事弄出来,让希拉里措手不及。于是她动用她的资源,让司法部长(比FBI高一级)澄清说邮件没有泄密的行为。这时候特朗普抓住了把柄:第一,这个事情是有的;第二司法部长出来澄清,那就是希拉里这些人欲盖弥彰。一下子翻盘了,这时候很多人更加怀疑民主党、特别是希拉里的诚实度。三、特朗普上台利用的是美国白人工薪阶层的文化怀旧 八年以来,白人中产阶级收入没有增加,社会不公加剧。八年的经济增长最终没有给弱势群体带来什么收入,特别是工业比较落后、白人集中的的乡村地区,甚至有一些种族主义情绪。美国社会在这次大选中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分裂,白人和移民之间的分裂,(当然白人和黑人、一些老的移民也是有不同政治倾向的)。希拉里的团队和她的支持者里更多是有色人种,移民、拉丁美洲人的后裔等等。这些人从文化上来说,跟美国传统文化之间有一定的差距。美国传统观念包括同性恋不能结婚、不应堕胎等,还有基督教信仰。比较新的观念,即所谓“政治正确性”,是不能歧视有色人种、不能歧视妇女、不能歧视同性恋者、不能歧视信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的人等等。特朗普那些人觉得凭什么要遵守这些思想?实际上文化问题跟宗教、种族、族群这些非常有关系。 精英支持希拉里,支持民主党的人比较多。几十年来,民主党在知识分子、大学教授、青年学生里都是占主导地位的。可是在高收入人群中是分裂的,比如传统石油产业、军队里也有不少支持共和党。过去支持共和党更多的是传统的富人、白人,现在一些白人开始贫困化了,所以阵线就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内不是那么分明了。一部分支持特朗普,一部分人支持希拉里,还有一部分人支持谁?支持民主党里的桑德斯(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其实美国的社会主义跟我们相差很多,不过桑德斯相对来说更主张平等、更加注重穷人的利益。结果这些支持桑德斯的人,后来一部分偏向了特朗普。当然桑德斯本人最后出来是支持希拉里的。 不管怎么说,最后特朗普当选利用的是美国白人工薪阶层对于移民的恐惧和对于过去逝去时代的文化怀旧。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写过一本书——《我们是谁》。他说,我们是谁?我们是美国人,但美国人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是盎格鲁—撒克逊的后代,至少是欧洲白人为主,以新教徒为主的传统社会。如果更多人加入美国,像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的选民群体里那些新移民或者老移民,他们不一定信仰盎格鲁—撒克逊人所信仰的那些东西,那么美国就不再是美国了。现在支持特朗普的人,有一种怀旧——几十年以前的美国人多么纯真!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种族、共同的宗教背景,有一种美国的向心力。现在这种向心力被外来的人和所谓“政治正确”的人占领了,他们很不满意。特朗普上来过程中就一直在攻击所谓的“政治正确”。这个可能全世界都有,我们叫身份认同的政治(identity politics),现在这种身份认同的政治某种程度上已经取代了钱包政治。当然钱的问题、阶级问题也很重要,但阶级的问题和“我们是谁”、我们是哪个种族、我们是谁的后代等等这些问题结合在一起,跟宗教的问题也结合在一起。这是我对美国现代政治——特朗普上台原因的一种分析。文章选自腾讯思享会,2017年2月19日
2017年3月21日 -
梁锦松:香港未来重在“聚才”与“聚财”
2017年3月16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前香港财务司司长,香港南丰集团董事长梁锦松先生在CCG北京总部发表主题演讲 今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自香港回归以来,得益于与内地间日趋密切的经贸和人文交流,香港GDP总量、人均GDP等指标总体呈增长态势。近年受全球经济大环境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香港经济增长率逐年放缓,出现金融服务业等支柱产业增长乏力、人才外流等现象。比起内地或竞争对手新加坡,香港还是慢了些。过去20年,香港人均GDP大概每年增长1.6%,而新加坡差不多是3%。 尽管如此,香港在发展经济方面,空间仍然很大。香港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20年来一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香港是中西文化汇聚的地方,法治健全、政治廉洁、税率较低,也是全球犯罪率最低的地方之一。香港还是人流、物流、服务流、资金流、信息流最繁忙的地区。有权威机构做过研究,五“流”最融通的地方,往往经济发展潜力最大。 “聚才”“聚财”对香港来讲最实用,人才尤为重要。在过去的7年中,西方中央银行大都在印钞票,钱在某种意义上是现在最不缺的资源,反而知识经济最缺的就是人才。香港应成为全球精英乐意聚居和工作的地方。在西方民粹主义当道,对外来人才采取排斥政策的当下,特区政府和工商界应派专人,点对点地说服国外精英人才到香港工作、居住,因势利导推动由应试教育向创新教育的转型。香港总人口不应只有几百万,而应成为一个拥有1000万人的国际大都市。若没有这个体量,香港很难支持国家在各个方面的发展。 当然,“聚财”仍然非常重要。每个时区都得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在可见的将来,亚洲这个时区应该还是香港和新加坡竞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出意外的话,中国将会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届时若依靠新加坡为金融中心,可能会有国家安全风险。现在全球IPO头十家企业,6家在美国,4家在中国,但只有1家在香港上市。香港应积极调整金融规则和产品,以支持国家发展。香港人需要看到,在“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过程中,中国的资本项目短时间内还做不到完全自由兑换,这意味着会形成境内、境外两个资金池。这两个资金池的风险对冲管理跟流动,会成为香港金融业的发展机遇。 为“聚财”,香港还应大力鼓励“三创”(创新、创意、创业),吸引高端研发机构到香港,大量吸收“三创”人才。香港应积极跟珠三角——尤其是深圳、东莞、珠海,开展突破性合作。应该想办法把香港制度上的优势——包括知识产权保护、自由市场、低税率等,跟深圳的体量,深圳、东莞所拥有的全球最好的制造业平台,以及珠海干净的空气土地相结合。若果真如此,我们就有能力打造能跟美国湾区竞争的粤港澳大湾区。在推动过程中,特区政府应注意与内地相关部门沟通,为“三创”人才流动创造便利条件,比如设立通关“金色通道”、突破港人外国人在内地逗留超过183天须缴内地所得税的限制等。 未来十年是香港承先启后的十年。有国家的支持,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有新老香港人和外来人才共同努力,只要新一届政府能跟市民充分沟通,提出一个清晰的发展规划,减少在政治上的不必要争拗,香港经济一定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民生也会得到改善。随着香港人幸福感的提升,对国家的爱护也会增强。在这个地缘政治局势多变的不确定时代,香港有能力为国家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者是香港南丰集团董事长、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前司长,本文整理自作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的演讲)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7年3月18日
2017年3月21日 -

【China Daily】Wang Huiyao: More talks should be held with TPP nations
About Author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Forging ahead with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will help China share the benefits of new round of globalization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said on March 15 at a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ews conference that China, as a beneficiary of globalization, will take an open attitude toward regional free trade arrangements that concern it and, where conditions are in place,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of globalization through opening-up.Indeed, China has been a strong advocate for the spirit of free trade that embraces openness, inclusiveness and mutual benefits. Recently this spirit was seen in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meeting of countries signing up for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in the Chilean town of Vina del Mar on March 14 and 15. China’s presence stirred a widespread assumption that it will fill the vacuum left by the withdrawal of the US and save the TPP from bankruptcy.Wendy Cutler, former US chief negotiator of the TPP and now vice-president of the 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 said that the TPP was not anti-China and was always open to other countries. It was initiated to liberalize Asia-Pacific trade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es in this region, she told a seminar co-hosted by the 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 and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on March 13 in Beijing.My personal observation is that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the trend of de-globalization we should fully recognize the anticipation of Asia-Pacific countries that China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TPP, seizing the chance to take part in further negotiations and meetings to take advantage of a mature trade agreement.First, it will help China share the dividends of a new 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Joining the TPP will provide a better channel for Chinese firms to outsource technology, services, telecommunications, banking, e-commerc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other sectors, to fully participate in global service trade and protect intellectual property.Second, compared with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the TPP has already formulated a mature framework. RCEP was initiated by ASEAN countries in 2011, and still faces a number of challenges. At the recently concluded RCEP meeting in Japan, rapid progress was not made. It takes time to achieve consensus. Hence,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meetings with TPP countries may create a chance to forge ahead with the reform of RCEP and furth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AP), adding new impetus to regional and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Finally, participating in the meetings with TPP countries could serve as a new economic input for Asia-Pacific free trade discussions and help China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global governance, which in return would help to thoroughly implemen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y improving geopolitics and deploying economic foreign policy.From China Daily, 2017-3-17
2017年3月20日 -

【China Daily】HK should tap bay area for development, says ex-finance chief
Antony Leung Kam-chung delivers a speech at a round-table seminar held by think tank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in Beijing, March 16, 2017. [Photo provided to China Daily]Hong Kong should find ways to conduct "breakthrough" cooperation with mainland cities like Shenzhen and Zhuhai and work together to build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said former finance chief Antony Leung Kam-chung at a round-table seminar held by think tank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in Beijing on Thursday."When we signed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EPA) in 2003, our cooperation became ’closer’, so now we should aim for ’breakthrough’ ones," said Leung, currently CEO of property developer Nan Fung Group.His idea also resonates with the plan outlined in this year’s Government Work Re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city cluster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This year will mark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Hong Kong’s return to the motherland. Leung said the next 10 years will be key to the future of Hong Kong.As one of the most globally connected regions, Hong Kong’s future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emerging trends. Leung used "VUCA", namely vulnerable, unclear, complex and ambiguous, to describe the future world, which is under great impact from new technology, globalization, aging population and so on.So he proposed that Hong Kong should make use of its advantages, take measures to attract global talent, encourage innovation, creative ideas and entrepreneurship, as well as actively take part in the Road and Belt Initiative.From China Daily, 2017-3-17
2017年3月20日 -

【财新网】美前TPP谈判代表:TPP未来或重回美国
卡特勒3月13日在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亚太经贸展望”研讨会上表示,“我个人看法是,在某个时间点,TPP会重回美国。这何时会发生,以何种形式,我不知道。但我对此很乐观,因为这是个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好协议”。 “我个人看法是,在某个时间点,TPP会重回美国。这何时会发生,以何种形式,我不知道。但我对此很乐观,因为这是个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好协议。” 美国前代理副贸易代表(Acting Deputy USTR)、前TPP谈判代表、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华盛顿办事处副主任卡特勒(Wendy Culter)3月13日在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亚太经贸展望”研讨会上表示。 “美国宣布退出TPP,我个人感到很失望,”卡特勒13日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举办的“亚太经贸展望”主题研讨会上表示。“我从未想到我们会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支持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而美国总统却在强调‘美国优先’,抨击美国的贸易协定。” 卡特勒表示,现在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依然“还未成形”(work in progress)。“美国过去20多年对自由贸易的支持,现在似乎正面临质疑。我们的向前之路目前还不清晰。从积极方面来说,美国政府承认贸易与投资的重要性。但我们接下来几个月可能面临一些冲突,但事情会随着时间和内阁成员确认入职而逐渐平息。” 3月14至15日,中国政府参加了在智利举行的“亚太一体化倡议高级别对话:机遇与挑战”会议,原本是拉美4国组成的“太平洋联盟”的一次峰会,智利政府邀请TPP签约国及中国、韩国参与今年会议。 卡特勒对财新记者强调,在智利的会议并不只是探讨中国和韩国是否想要加入TPP,“是比这个更基本的问题”。卡特勒表示,智利邀请TPP国家及中国和韩国是为了探讨美国退出TPP后亚太地区如何在贸易上向前推进。“因此,我不认为这次会议将发布重要决定。”卡特勒认为此次会议是亚太地区必要的一次对话,来探讨向前推进的最好方式。是开展双边贸易,还是尝试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下与现存成员国继续推进TPP,或是微调TPP并容纳中国和韩国等其他国家,这些问题都将是会议讨论的范畴,均需详细的讨论。“我认为每个国家都需要决定什么方式是符合自身国家利益。” 卡特勒曾表示美国退出TPP会留出“真空”(vacuum),中国或填补这一真空。但她对财新记者指出,这种“真空”并不是指中国取代美国领导TPP,而是在亚太区域的贸易领导地位。“美国退出TPP,表明美国将不会领导自贸协定。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承担一些领导责任,这符合逻辑。” 3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见采访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中外记者时表示,维护全球贸易的自由化,“这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因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我们对已经达成或者希望达成的一些区域贸易安排一直持开放态度,也乐见其成”。“关于区域的自由贸易安排,涉及中国的,有条件的,我们持开放态度,愿意去进行推动。我们不会越俎代庖,不会超越区域去做不应是中国做的事情”,李克强表示。 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首席谈判代表、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研讨论上回忆,TPP最初谈判时就有声音称其设计初衷是反中国的,但几年前卡特勒就坦诚回复自己,TPP背后并没有反对中国的阴谋。 龙永图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对TPP的解读要专业化和去政治化,否则会误导大众。“贸易就是贸易,不要与政治因素混淆。”对于中美贸易,相信共同的利益会把各方联结起来。贸易摩擦可以存在,但要尽力避免严重的贸易冲突,甚至贸易战,这将同时给双方带来损失。龙永图总结道,过去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基于共同利益合作,就会找到解决办法。 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何宁在研讨会上强调,看到中美双边贸易关系时勿忘中美都是WTO多边贸易体制的成员。何宁表示,中国加入WTO最大的红利,不在于贸易伙伴对中国的贸易减税,而在于加入WTO后中国与其他成员国家在多变贸易体制下的约束关系;正是这种约束关系使中美贸易保持稳定。 卡特勒对此表示“完全赞同”。中国加入WTO,使中美双方需共同遵守一系列规则,这有助两国解决潜在的贸易冲突;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这都是加入WTO的积极意义。“但是,近年来,美国国内认为中国放慢改革和市场开放的步伐,也有一些迹象使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开始将投资机会对外资关闭以促进国内产业发展。”卡特勒对财新记者表示,“我认为两国政府需要尽快坐下来好好讨论这些问题。” (记者 张琪)文章选自财新网,2017年3月16日
2017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