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信刚:检视区域研究 寄望丝路探索
2017年4月20日
一、检视区域研究
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始于冷战时期的美国,可以被视为东方学的近代改良版。美国在19世纪除了奉行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把拉丁美洲视作后院,并没有积极参与海外殖民地的争夺。所以美国学界虽然很熟悉欧洲和美洲,却没有东方学的传统。从西柏林被苏联封锁和朝鲜战争开始,美苏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双方都想了解对方,也都想争取新近独立和即将独立的亚非洲国家进入自己的阵营。
这时美国精英阶层体认到,美国政府和商界亟需大批通晓世界各国语言与文化的人才。1951年,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邀请二十几间有实力的大学齐集会议,建议这些大学成立以不同区域为对象的跨学科的新专业,如东欧研究、中东研究、东亚研究等。这个建议与美国大学传统上以学科分类的架构不符合;美国大学一般以学科分院系,每个系的重心放在一种或两种专业知识上,比如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和考古学、经济学等。过去美国学者对于东方的研究是在专业下进行,因此研究中国政治的人一般是在政治系里,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则属于经济系。
一些学者起初抗拒把不同专业混杂起来培养学生的方式,认为这会让学生专业素养不足。但是福特基金会认为美国需要许多对各地区的历史、社会、经济和政治有一般性认识的人,所以拿出巨额款项在这些大学设置了区域研究奖学金,吸引学生进入区域研究;不久美国政府也通过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拨专款资助学生学习某一种语言或是某一国的历史文化。当时有学者无奈地也调侃地归纳出一条法则:The Golden Rule of Science is he who has the gold makes the rule!(科学的黄金法则是谁有黄金谁就定法则!)
1965年以后,欧洲人开始的东方学在北美洲兑变为区域研究;要培养的是对某一个地区(或国家)有一般性认知的人。钱能说话(Money talks!),到了1975年,北美洲的一流大学几乎都建立了若干区域研究的专业。
在1965-75这段时间里我与北美洲三间大学的区域研究有过交集;之后二十多年里我在法、加、美四个大学接触到不少区域研究的学者。

胡佛总统
我修读硕士和博士的斯坦福大学和西北大学是早期建立区域研究中心的大学。斯坦福大学位于太平洋东岸,因为第一届毕业生胡佛(Herbert Hoover)总统曾在中国开滦煤矿任工程师,所以很早就重视对东亚的研究。我时常去资料丰富的胡佛研究院(Hoover Institute)看中文书,包括当时美国邮局不递送的《人民画报》;我的美国室友因为与我结识而对中国发生兴趣,选修了中文课程,后来在台湾和珠江三角洲做过不少田野调查,成为研究中国民间宗教的权威学者。西北大学有一个很强的非洲研究中心,和苏丹有交换学生的协议,所以不少苏丹的精英在西北大学受教育。早我一年得到工程博士的一位苏丹同学回国没有多久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
1969-76年,我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认识一位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他学过两三年中文,能说简单汉语。有一次他提到一位陈先生,我问这人中文名字怎么写,他书写时把“陈”字写错了——“东”字在左边,“耳朵”在右边。看到这位“中国通”写错的“陈”字,我意识到汉字的确很难:“郑”和“郭”这两个姓氏的耳朵都在右边,为什么“陈”字的要在左边?何况,“够”也可写作“夠”,两边可以互换!
1976年我转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医学院任教,大学里有一个伊斯兰研究院(Institute of Islamic Studies)。1981-82年我在巴黎大学任客座教授,这段时间我对伊斯兰文化开始产生兴趣。回到麦吉尔才知道这个享有盛誉的研究院始于1952年,受到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应该是从东方学向区域研究转型时期的产物。
1984年到1990年我在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任教授及系主任;有三年时间被选入全校的长期聘任与升等委员会(University Tenure and Promotions Committee),参加过区域研究教员升级的评审,因此也涉及区域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标准。
当时在美国学术界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主流认为区域研究名为跨学科,但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什么都知道一点,但没有一样真通,这样的人日后如果担任教员不太可能做出有意义的学术创新。我很能理解这种批评,因为我的专业生物医学工程素来就是注重跨专业的学科。1988年我就任美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会长时,强调我们必须或者是兼通生物医学的工程专家(如仪器设备),或者是兼通工程的生物医学专家(如心血管病专家);作为大学教员,我们的论文必须要能刊登在工程专业或是生物医学专业的学刊上,否则我们只能站在两个学科的外面朝里看,不能成为跨学科的桥梁。因此,我在委员会甄审升级个案时的立场是,要获得长期聘任(tenure)的从事区域研究的教员必须在某一个传统学科里又有优良表现,而不能是“Jack of all trades, master of none”(样样通,样样松)。
第二种意见认为,各个区域研究作为新兴学科时间不长,还不能清楚订出“某区域研究”的学术标准。但是,学术界总归会对这个当初由外界力量带进校园的新事物赋予足够的知识内涵;过于实用而缺少学术内涵的课题应该由政府机构、专业智库或是大型企业做。在达到这步之前,甄审不应该过于严苛,以免把可能成为优秀学者的人过早淘汰出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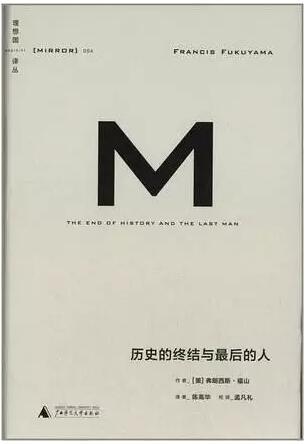
《历史的终结》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9月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强力推广经济全球化和近代西欧发展出来的议会民主制度,弥漫着天下一统的乐观期盼,如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之终结》所预测的那样。但在911之后也有文明冲突不可避免的论调,如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96年出版的《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里所指的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儒家文明的较量 。正在此时,我应聘担任有三百年历史的匹兹堡大学的工学院院长兼医学院教授,受命以生物医学工程协助振兴这个美国的“钢铁之都”和老工业基地。当时匹兹堡大学的两大强项是医学和区域研究。恰巧,我和这两个领域都有渊源。

中国上古史专家许倬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我在匹兹堡时常往来的是两位历史学家:中国上古史专家许倬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和通晓汉文和满文的清史专家罗友枝(Evelyn Rawski) 教授(夏威夷出生的第四代日裔美国人)。罗友枝教授的夫婿是经济学教授Thomas Rawski 。我与他们二位在1995-96年间有过几次聚谈。有一次在他们家里吃过烤肉后,罗友枝教授向我透露了她不久将震撼东亚史学界的“新清史”观点:满清王室者并没有同化于汉文化,而是以不同的身份和方法统治多民族多文化的满清帝国;汉族为主的中国仅只是这个帝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学术观点,我直觉上不赞成,但自己没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无法反驳她的说法,而她却告诉我她曾经大量阅读清廷军机处的满文档案和宫内活动的记录。这说明,一个学者要对中国历史做出新的论述,必须要有相当的功力与准备。我回答了她关于蒙古、新疆和西藏不属于中国的说法。我的理据是:八国联军之后,清政府被迫承诺四万万两白银,其根据是当时包括新疆、蒙古、西藏在内的中国共有四万万人口,这笔巨大赔款由包括新疆、蒙古和西藏在内的各地分担;这是历史事实。辛亥革命后,列强要求中华民国政府承认大清帝国签订的全部国际条约(包括赔款与租界)。既然中华民国要承担大清帝国的全部条约义务,为什么不能继承清帝国的全部领土呢?这个事例说明,区域研究者需要专精(比如要能阅读满文资料),也不能不从多个角度看问题(比如要知晓外交史和国际法)。

罗友枝教授 第四代日裔美国人
我和罗友枝教授辩论“新清史”观点时,一场更大的辩论正在北美洲进行。那就是区域研究是否应该继续发展?
经过五十年的发展,美国的区域研究已经人才辈出。但是一部分学者在冷战结束后逐渐把精力转移到世界性的问题上,认为具有全球性质的现代化和民主化问题,全球气候变化和难民问题都超越了区域研究的范围。今天,在美国的大学里,区域研究已经不如30年前那么受到重视了。但我认为,只要区域特征能够影响未来发展,区域研究就不会失去意义。问题只在于,区域研究的方法是否够严谨,成果是否具有持久价值?
二、寄望丝路探索
“一带一路” 倡议反映了当前世界的新格局,表达了中国对国际关系的设想。它着眼于英国学者麦金德所称的“地球岛”——亚、欧、非三洲,建议为促进亚洲各地区间,亚欧之间以及亚非之间的联系而强化陆上及海上的交通;为进一步发展各地经济而兴建各种基础设施,更主张各国依平等原则,共商共建共享。为此,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将对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同样提供资助。从发展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一带一路“ 倡议或可被视为“三个世界”理论的修订版和实质化。
四十年前,中国国民中到过外国者少之又少。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2016年出境的中国国民已达1.2亿人次,常住外国者也有数百万。但是如果盘点一下中国目前熟悉丝绸之路地区的人才和他们的知识总量,情况并不能令人满意。
丝路(Seidenstrassen;亦称“丝绸之路”)这个名词是德国地理学家菲迪南. 李希特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于1877年首先提出来的。他受德国政府的委托,建议一条连接德国和中国的铁道路线;为此他实地考察了中亚、东亚和东南亚,选择了一条贯穿欧亚大陆的路线,就是他心目中的古代丝路。
一百四十年后,连接中国和德国的现代铁路已经成为现实。这只是促进丝路各国互助合作,进一步发展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初步成绩。要真正实现“一带一路”倡议,还需要更多资金和技术,国际支持,特别是通晓丝路情况的人才。
对中国来说,首先需要大批对丝绸之路各地区各国家的地理、历史、语言、社会、政治、经济等有一般认识,又具有某方面专长的人才。这样的水平一般可以在本科毕业时达到;其关键是课程的设计和教学质量的保证。其次,需要数量颇大的,能在特定领域研究某个区域或国家的人才。这应该需要完成硕士学位;通过访问、实习或在地任职,他们应该具有与某一地区或国家的人民和政府顺畅交往,共同工作的能力。最难培养的是将来能在政府、智库、工商企业和高等院校工作的有专精知识,能提出新问题,做出新学问的人才。这些人应该需要攻读博士学位,最好再经过一段博士后训练。
作为丝绸的故乡,丝路的起点和“一带一路”的倡议者,中国需要用知识和善意赢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人民的信任和尊重。中国的高等院校在这方面确实责无旁贷。
目前中国高等院校关于西亚和非洲的人文课程主要是传授18-20世纪欧美学者所积累的知识。但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的考古和历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外语教研方面也有出色的表现。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学界应该与本地学者合作,在丝路各国展开考古与历史的深度研究。
亚洲和非洲比欧洲的文明史要久远,亚、非洲各地一定拥有大量未曾发现的考古资源和历史资料。今后在丝路国家修建基础设施和进行地下勘查时,一定会有考古遗址出现;中国学者应该积极参与考察和保护这类文化遗产。此外,丝路沿线各地区和国家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间组织等也都有待进一步厘清。
在社会科学领域,本来就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适合各国情况的普遍发展模式。任何地区的发展与现代化都会受到地理、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学者若要认真地探索丝绸之路,就应该由“一带一路”建设中得到启发,开辟新课题和做出新论述。这不单是做学问,也是赢得丝路各国知识精英的尊重和信任的不二法门。

“一带一路”线路图
我认为,摆在中国知识界面前最大的挑战是通过对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地区深入的观察与分析,参照发达国家与中国自己的发展经验,建构一套“发展中国家应以合作互补来促进彼此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阐述在当今科技水平和国际新形势下的发展新途径。
无论是在人文还是社会科学方面,中国的高等院校都需要加强合作。但可能更急切的是校内不同院系之间的合作。目前各大学校内的组织架构和资源分配方式往往使不同的院系或是恶性竞争,或是不相往来。希望今后“一带一路”研究不会这样。丝路探索所需要的方法论和组织形式与各大学的传统科系架构一定会有差异。根据我在不同国家不同大学的观察,建立有学生名额指标并有相应预算的跨学科的丝路探索单位(中心,所,院)是一个合乎实际的选择。
有关部门可以参考美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验:投入可以有效使用的新资源是激励大学重整架构、促使大学老师调整心态的有效诱因。因此教育部及其他官方机构,以及准备在国外拓展业务的大型企业,都应该协助中国各高等院校完成培养人才和创造知识的双重使命。
虽然大学需要财力资助,有一点至关重要:高等院校的基本职能是培养人才和创造知识,不是担任政府或者企业的智库。不容否认,一如当初美国的区域研究,今天进行丝路探索确实具有现实性和功利性。但是丝路探索必须以治学的严谨方式为之;在进行与政策或时事有关的课题研究时,必须通过对数据的悉心搜集和科学分析得出客观结论。希望从事“一带一路”探索的学者们能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上把自己的研究与现实结合;切忌只对官方政策表态支持,甚至把研究报告视为写“策对”、上“奏折”。否则,这些学者就枉费了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错失了为中国,为丝路各国人民做贡献的机会。
文章选自腾讯新闻,2017年4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