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日报网】赵穗生:中美关系会在健康合作的道路上继续发展
赵穗生,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克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 美国政府近期针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举措,一度让中美关系变得紧张。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6月8日在全球化智库(CCG)发表演讲时指出,无论如何,中美关系还是会在健康合作的道路上继续发展。 赵穗生说:“1979年中美建交时,我在北大。1985年,我去了美国。我把我这样的人看作中美相互理解的一座桥梁,因为我们这类人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几乎占了人生的一半。相较于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我们对中国有更加切身的体会。而在美国生活了33年,相较于国内研究美国的学者,我们这类人又有在美国长期生活的个人体会。” 在赵穗生看来,尽管中美之间有很多摩擦和竞争,但合作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接触政策不仅仅是对中国有益,对美国也有益,美国也会是受益者。中美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其次,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在逐渐削弱,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增长。如果美国想要在这个地区继续存在,除了跟中国进行接触之外,没有第二个选择。再者,美国跟中国的接触保证了中国没有跟美国对抗。如果美国放弃接触政策,可能会创造出一个敌人。 他最后总结说:“我自己的判断是,中美之间虽然会有很多摩擦,竞争也是日益强烈,但是美国除了把自己的事情搞好、继续跟中国接触之外没有第二个选择。”文章选自中国日报网,2018年6月12日
2018年6月13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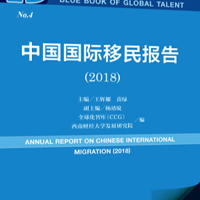
【新华网】智库报告:“来华逐梦”外国人数量呈上升趋势
新华网北京6月12日电(何凡)近日,全球化智库(CCG)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报告指出,我国正在从国际移民来源国,成长为治理方式与机制不断进步的国际移民目的国,“来华逐梦”的外国人数量呈现上升趋势。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成为中国移民的重要流向地区。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由总报告、中国篇、区域篇和专题篇四部分组成。报告以多元视角,对世界主要西方国家的移民现状与政策取向、中国的移民新政与治理方式等丰富内容进行全面梳理和深入研究,进一步解析了全球移民政策趋势、中国在全球移民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等紧密相关的议题。 该报告主编、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表示,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尤其是我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各类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的计划、政策的出台,对海外高层次人才回流或来华效果明显。而对支持各类人才计划实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我国出入境制度的不断探索与创新。 报告指出,根据汇丰发布的2017年《移居国外工作者全球报告》显示,中国目前处于汇丰全球职业发展排行的世界第二,外国人移居到中国可获得各类职业的优势。从就业前景认知与估计上看,外籍人士对中国内地的就业前景远高于对全球、对东亚地区整体的估计。 而根据世界银行2017年的不完全数据显示,中国2016年已成为世界第五大侨汇汇出国,连续两年处于前五名。这已能说明中国不再只是国际移民的来源国以及侨汇的汇入国,而是不断成为国际移民的目的国。 报告还称,在我国内地移民的前20大目的国中,有7个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加坡(44.86万)、孟加拉国(17.78万人)、泰国(10.03万人)、印尼(7.03万人)、俄罗斯(5.62万人)、菲律宾(3.6万人)和缅甸(3.37万人)。 报告认为,现阶段的中国外交取得了巨大进展,政府的派出机构和人员随之增加。同时,随着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国“走出去”的企业与其他相关机构也迅速增加。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派驻海外的劳务移民约200万人,90%集中在亚洲和非洲国家,其中绝大部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报告建议,借力“一带一路”的发展布局,构建区域国际移民治理的合作机制。除了可以通过吸引“一带一路”地区的留学生为本地区发展培养造就国际人才之外,我国还能与本区域国家一起,设立专门针对治理与援助本区域的非常规移民问题、共同规范与完善常规移民的基金与行动,由此为“一带一路”地区的移民问题建构一个区域协调应对机制,分享治理经验。文章选自新华网,2018年6月12日
2018年6月13日 -

【Global Times】Fewer Chinese emigrate to US, UK
China has seen slowing growth in the number of people applying for foreign residence or citizenship, a report released on Saturday showed. Developed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S, Canada, the UK and Germany, have seen fewer Chinese immigrants over the years, whil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 becoming more popular as immigration destinations, according to a report issued by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in Beijing.China is the fourth-largest source of immigrants in the world.The five most popular nations and reg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for Chinese are Singapore (448,000), Bangladesh (177,000), Thailand (100,000), Indonesia (70,000) and Russia (56,000), the report said. In 2017, about 74,000 Chinese were granted permanent residency in the US, 9.2 percent less than 2016. Only 2,271 Chinese applied for UK citizenship in 2017, the lowest number since 2007,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Tightening immigration policy in developed nations such as the US and Canada, as well as increasingly conservative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nts in the UK and Germany, have all been majors factors in this changing trend, Weng Li, a law professor at Zhejiang University, told the Global Times on Saturday at the conference on Global Talent Mobility, Migration, and Migration Law held in Beijing. Chinese immigrants are a major source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the report said. In 2017, an estimated $63.9 billion went to China from overseas workers, the second-largest after India. Driven by globalization, China has see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workers in foreign nations, mostly in Asia and Africa in 2016. Beyon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seas Chinese need to better serve China’s rise, Yan Ting, professor from Research Center for Overseas Chinese at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said at the conference. China must put forth policies that strengthen the links between ethnic Chinese and China, such as preferred visa policies and "Chinese origin cards," Yan said. From Global Times,2018-6-9
2018年6月12日 -
民间组织对外文化交流座谈会在京举行
2018年6月4日,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和中华文化促进会联合主办的“民间对外文化交流现状与思考”座谈会在国务院参事室召开。多名专家学者应邀出席会议,他们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田青;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国务院参事王京生;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国务院参事、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原党组成员樊希安;国务院参事、国务院研究室信息研究司巡视员忽培元;南南国际贸易促进中心主席耿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原副局长李勇;国际公益学院副院长黄浩明;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金锦萍;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办公室主任王珂。出席会议的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华文化促进会领导及工作人员有: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王仲伟;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副会长、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主席团咨询委员金坚范;主席团委员兼主席助理姚赛;国务院参事室文史业务司司长耿识博;中华文化促进会外联处主任韩阳;外联处副主任张月。座谈会由王石主席主持。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王仲伟做开场发言。文促会主席团咨询委员金坚范做最后发言。会议围绕民间组织对外文化交流的现状和思考展开了讨论。以下为嘉宾发言节选王仲伟 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我们应该带着中华文化去问候世界。增强跨文化理解的能力。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主持会议 王 名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我最关心的是孔子学院转型升级的问题。我会写出专题报告阐述此问题。耿 弘 南南国际贸易促进中心主席对外文化交流,应该放下身段交朋友,少讲官式语,多讲民间言。田 青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民间交流困难重重,光有良好愿望是不够的,必须有相关政策配套。陈平原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对外文化交流,不仅是输出,还要输入。王辉耀 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民间交流,需要抓手、品牌。如举办全球文化论坛,在一些国家举办中华文化节等。李 勇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原副局长政府要信任民间组织,对民间交流少一些限制,多一些鼓励。忽培元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研究室信息研究司巡视员民间组织和政府在对外交流方面,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应互为支撑,交相呼应。王京生 国务院参事搭建平台,为开展民间交流提供舞台。 黄浩明 国际公益学院副院长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是路修好了但桩子太多。在民间交流方面,现在桩子太多。樊希安 国务院参事、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原党组成员通过民间更容易进到“一带一路”国家里来,我们对外文化交流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多的作用。金锦萍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民间交流千万不要以外交为目的,不能功利性太强要高度信任,遵循规律。金坚范 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团咨询委员民间文化交流要注意培育当地的外国友人。文章选自中华文化促进会,2018年6月5日
2018年6月12日 -
王缉思:世界政治进入新阶段
纵观历史,世界政治趋势一直呈起伏不定的波浪形。本文提出“世界政治进入新阶段”,既是基于对世界历史的一种长线观察,更是基于对近年来世界政治发生的一些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的研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论证国际形势时,既坚持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传统观点,更突出了今日世界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实际上,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的内涵与外延都已发生变化。当今世界和平问题更确切的说应该是安全问题。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但安全挑战特别是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愈发突出。发展问题的外延扩大,除了经济增长以外,还更多地涵盖了社会发展与进步、国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提高、技术创新等诸多内容。“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果说冷战结束时天下大势以“合”为主流的话,新阶段的世界政治正在陷入巨大的漩涡,“分”的逆流迎面而来。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受到市场力量和技术力量的强劲推动,是任何国家和社会力量都难以逆转的。只要世界范围内的人口流动(包括合法和非法的移民、旅游、劳工、留学等)还在扩大,经济合作、社会交往、文化互动的规模就不会缩小。另一方面,在收入分配领域不平等、不公正现象日趋严重的情况下,社会认同的割裂将世界政治推向分化,形成反全球化的逆流。新阶段世界政治中的分化和分裂,是由两方面的长期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因素是经济不平等进一步扩大。当今世界上最贫穷的若干非洲国家,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00至500美元。最富裕的国家如美国、瑞士、新加坡等,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最贫穷国家的100多倍。随着经济收入差距的扩大,全球范围内其他方面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也是惊人的。一些资料显示,无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国家内部,现阶段全球范围的经济不平等,均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加剧世界各国政治分化、分裂的第二个长期因素,是全球范围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社会认同的重新组合。当今世界上有3亿以上人口长年生活在其出生地以外的国家,另外还有很多跨越国界的季节性劳工,各国的国内流动人口就更多了。人们生活在异国他乡,或者在自己生活的地域发现越来越多的肤色、文化、信仰不同的外来人口,会产生更大的乡恋、疏离感和排外情绪。网络、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方便了人们找到同胞、同乡,或者结成价值观上“志同道合”的“知音”和“朋友圈”。这种现象,实际上割裂了种族、族群、教派、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社会认同,加剧了许多国家政治的极化。上述两个长期因素的结合,即经济不平等沿着社会认同的断层线加剧,构成了世界政治新阶段的若干特征。 1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并同时上升近些年来,民粹主义思潮对冷战后曾经占有强大话语优势的新自由主义形成猛烈冲击。民粹主义可以帮助那些被政治精英和传统政党忽略的弱势群体表达自己的心声。但是,民粹主义缺乏公民个人尊严与个人基本权利的观念。民粹主义者反对权威,但他们中间很多人又容不得反对派,甚至容不得“旁观者”。民粹主义对既有政治秩序形成新的挑战,加剧了国家内部的政治裂痕。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可谓孪生兄弟,相互呼应,同时上升。民粹主义者多认为,本国的精英是外国人、外国资本或者难民的代言人,不能保护本国人的利益。民族主义有着情感上的煽动性和内部凝聚力,民粹主义则有道德上的合理性和感召力,二者合力更加具有政治颠覆性。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通过呼吁“美国第一”等口号当选美国总统,皆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相互融合的产物。法国的国民阵线、德国的选择党、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澳大利亚的单一民族党、新西兰的优先党、奥地利的自由党等,都带有右翼民粹主义色彩和反移民倾向,近年来都在本国获得了更大的政治能量和支持。民粹主义在国家之间造成的裂痕,在东西欧之间表现得尤其明显。在许多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曾经对欧盟抱有很高的热情与期待。但随着民粹主义的兴起,东西欧之间似乎又一次筑起了一堵高墙。同西欧相比,民粹主义政党在中东欧国家的势力更加强大。已经获得执政地位的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捷克“不满公民行动”,都对欧洲一体化持保留态度,反对欧盟被德法等大国主导,不愿意接收难民。这些政策立场,导致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及其西欧成员国之间的离心力越来越强。 2威权主义和强人政治回潮民粹主义的来源是人们普遍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主要不是来自战争和暴恐行为的威胁,而是来自相对收入下降、就业和社会福利无保障、教育机会和医疗待遇不平等、环境污染等与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人们对全球化、现存政治建制的怨言越来越多。民族主义情绪下的怀旧意识和复兴愿望开始复苏。多数伊斯兰国家在认可民主化的同时反对西方化。伊斯兰教义与西方世界观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在世界历史上,财富分配严重失衡每每引发战争、叛乱或暴力革命。使用暴力手段“均贫富”的结果是“均贫”而非“均富”。但是现在即使通过类似手段实现表面上的“社会公正”,其可行性、有效性、道义性都非常低。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共同作用下,人们往往寄希望于权力集中的政府以及强大而决策果断的政治领袖,来领导他们恢复民族荣耀,凝聚国家认同,并采取强力的措施来改变不公正现象。冷战后采用多党制的“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不断发生种种乱象,包括贿选、腐败、暴力冲突、政治对立等等,为威权主义的复归和强人政治的回潮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当今世界政治中的“强人”,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捷克总理巴比什、印度总理莫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埃及总统塞西、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等等。这些强人的个人背景、政策偏好、从政经历、领导方法有很大差别,但都有鲜明的个性,都在一定程度上鄙视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善于利用本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与国家社会制度的示范效应相类似,强人政治也有示范效应。几年来世界政治中的强人不断涌现,绝不是偶然的。随着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发达国家在许多方面的优势不再像冷战结束前后那样明显。在威权政体加强本国形象宣传和社交媒体日益发达的作用下,西方国家的软实力遭到侵蚀,西方媒体的话语权受到强烈的质疑和抵制。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人口在全球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以相当快的速度向后者倾斜。由此看来,威权主义和强人政治的回潮将不是短暂的历史现象,而可能代表着世界政治新阶段的重要特征。 3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战争危险冒头在传统的意识形态影响下降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正在各国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正确性”。一个政党或政治派别、一位政治领导者的对外政策表态越强硬,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越强烈,就越容易得到国内政治支持。这一倾向表现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是贸易保护主义和限制移民政策;表现在国家安全方面,则是增加对社会安全(国内维稳)和国防的投入,加剧地缘政治竞争。今日全球各地的地缘政治竞争方兴未艾。特朗普政府公开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久拖不决,而且有可能激化为军事冲突。美欧几次使用武力干涉中东、北非国家的内政。叙利亚、也门等国的内乱还在继续,巴以冲突激化,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剑拔弩张,北约国家同俄罗斯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对立看不到缓解的希望。军费开支是国际安全形势,特别是军事安全形势的风向标。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大幅增加本国的国防预算,加速发展武器装备,提升军事实力。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2017年全球军费达到冷战后的最高值。美国2018财年的国防预算较2017财年约增长10%。中东和亚太是全球军费增长最快的两个地区。中东地区国防预算每年都保持两位数增长。中美在西太平洋的军事竞争加剧,亚太地区国家的不安全感上升,纷纷加大军费投入。日本军费开支自2013年以来连续6年增长,印度2018年国防预算增长超过8%。 从全球层面看,各国在国际上的不安全感往往同国内政治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互为因果。某些国家的国内治理不善、社会分裂和经济停滞,同国际关系层面的利益冲突相互交织,对全球安全秩序将造成巨大冲击。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重大问题,不仅是“新冷战”会不会在中美两国之间爆发,还包括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的军备竞赛,会不会使全球的长期和平稳定局面出现逆转。 4技术创新是双刃剑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互联网金融、大数据应用等技术进步,为人类生命和生活带来诸多好处,但也孕育着很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例如政府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审查和监控的行为,冲击着言论自由、隐私权观念;改善人类基因的技术也引发了道德争议。本文所描述的“世界政治新阶段”,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它也许是20世纪晚期开始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中的一段间奏,但也许会成为一个不稳定的新时代的序曲。许多国家正在发生的政治公正缺失、社会裂痕加深的现象,国际舞台上愈演愈烈的经贸摩擦、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争夺,还有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技术革新的负面作用,都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警惕。文章选自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2018年6月10日
2018年6月12日 -

【中国新闻网】变迁与转型 华侨华人成为国际移民重要组成部分
中新社北京6月10日电 (周乾宪)全球化智库(CCG)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9日在北京联合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指出,中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移民来源国、第二大侨汇汇入国。 “华侨华人是国际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务院侨办侨务干部学校副校长赵健提到,中国人移居海外主要有三次大的浪潮。前两次源于西方人进行贸易扩张和殖民地开拓,对中国商贩和劳动力需求巨大,形成了“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的格局。 “第三次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放宽乃至取消对海外移民的限制,形成了‘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的态势。”赵健说,早期的华人移民最擅长餐馆、理发和建筑这三种职业,而年轻一代的“新侨”大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律师、医师、工程师成为他们新的职业追求,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亦不断加深。 报告中提到,根据联合国经社部关于国际移民存量的数据,2015年,世界各地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964.61万人。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是中国大陆移民的五大目的国。同时,前20大目的国中有7个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张振江告诉中新社记者,“一带一路”相关地区历史发展迥异,文化政治经济皆不同,各地的华侨华人社会也各有特色和优势。 因此,张振江认为,应针对各国的实际情况,以华人社团、华文媒体作为支点,分重点、有层次、张弛有度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还显示,目前,中国移民迁出量增速放缓,移民美加英德的人数连续下降。 “这一方面是因为上述国家对移民的态度有所变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以及对国际人才引进力度的加大。”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说道。 他表示,中国出入境政策创新成果卓著,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不断发展,入境、过境制度更加便利与完善,出入境人员统计门类增加,近期还正式组建了国家移民管理局。 其中,外籍华人获得不少专属条款。例如,今年1月22日,公安部推出八项出入境便利措施,外籍华人出入境签证由之前最长1年放宽至5年内多次有效。 又如,2016年公安部推出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对具有博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或在中关村长期创业的外籍华人提供申请永久居留的便捷通道。上海、浙江、广东、福建等地也陆续出台相关政策。 美籍华人、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尹晓煌对记者说,如今,身居海外的华侨华人不仅可以当“海归”,也可以是两头跑的“海鸥”和“海燕”,以自身便利的各种形式到中国创新创业或者离岸“孵化”,既调动了华侨华人的热情,也为中国自身发展创造更多机遇。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8年6月10日
2018年6月12日 -
朱锋: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伙伴关系
专家简介朱锋,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亚太地区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荣景,并在人力资源上紧密相连。尽管还存在一些闪火点,如朝鲜核问题、南中国海争议、中日钓鱼岛/尖阁诸岛争端,该区域在全球政治已经显著发展为新的权力中心。没有多少人会怀疑亚太地区在21世纪作为重要巨头的潜力。但是,亚太地区的持续和平、繁荣和稳定并非是必然的。随着主要国家在亚太地区加强竞争,区域安全形势变得越发复杂。可信和可行的出路之一,是不断扩大区域的相互接触和伙伴关系。中国于过去20年来就在这么做。 中国同本区域的接触,开始于19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政策。近40年来,中国的经贸措施深获区域国家欢迎。如今,在亚太经合组织的21个成员当中,中国是19个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外交上,没有任何亚太国家不同中国建立关系。就算是南太平洋的岛国,都把中国视为主要的外部经济联系。中国在那里的影响力已经显著超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北京要深化接触的最新举措是“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航道、输油管和制造业基地强化连接。“一带一路”无疑是中国要把区域的商务和社会更紧密结合的战略。其发展前景还不明确,但中国要扩大区域影响力的用意则不容置疑。 “伙伴关系”在中国的外交语境有特殊的意义,是相对于美国的“同盟体系”的“中国选择”。北京称之为“结伴”来区别于“结盟”。中国自豪地宣称,自己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全球伙伴系统”,来突出中国光鲜的国际形象和增长的影响力。 中国的外交词汇有不同的说法来形容各种伙伴关系。例如,中国和亚细安在2008年宣称,它们的关系已经从“战略对话伙伴”升级到“战略伙伴”。中国和韩国的关系则是“战略互信”伙伴关系。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在2008年安倍首相第一任期时是“战略互惠互利”伙伴关系。虽然两国面对领土主权纠纷和安全问题的困扰,中国总理李克强2018年5月时隔八年后访问东京时,重申了双边关系的特质。当然,最重要的伙伴关系有两个:同俄罗斯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以及同巴基斯坦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该如何理解中国这些形形色色的伙伴关系?这显然并非易事。至少,这些不同词汇反映了中国对建设“伙伴关系”的重视。 对于中国而言,建设“伙伴关系”的最大挑战就是同美国的具体外交关系。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1998年访问北京时,双方一度宣布双方将努力建构“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这证明是两个大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就双边关系所提出的最积极的定义。不幸的是这仅是“昙花一现”。自克林顿以来,没有美国政府愿意用“伙伴”的战略层次来形容和中国的关系。反讽的是,特朗普政府反而在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用“战略上的首要竞争对手”来形容中国。 北京和华盛顿难以用“战略伙伴”来形容彼此的关系,形象地展示了两国在合作之际越来越大的竞争。但是,这不应阻止两强在亚太地区承担彼此重大的责任,减缓军事紧张并追求可行的稳定与繁荣的目标。两国军方尤其应当实施全面的沟通与合作。 中国的“接触和伙伴关系”攻势积极且持续推行,但真正的考验不在于北京的论述,而在于其实质成果。面对各种领土纠纷的反弹、关于其“强势”的指控,以及外界对中国在区域享有优势的困扰,北京更愿意采取谨慎和有建设性的外交攻势。推动解放军在本区域的交流,应该不会导致对其战略意图的误解。此外,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谈判上,与亚细安诸国取得法律上及战略上的实质进展,也是中国“战略伙伴关系”是否能真正取得成果的另一观察指标。文章选自联合早报中文网,2018年6月5日
2018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