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引发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例如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使得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
- CCG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
- CCG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
- CCG一带一路研究所
- CCG世界华商研究所
- CCG数字经济委员会
- CCG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图片
- CCG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图片
- CCG世界华商研究所图片
- CCG一带一路研究所图片
- CCG数字经济委员会图片
- 成为系列论坛会员
- 成为系列论坛会员联系
- 概况介绍
- 兼职研究员
- 未分类
- 概况
- 全球化
- 全球治理
- 美国
- 国际人才政策
- 中美贸易
- 国际教育理念与政策
- 中国开放指数
- 新闻动态
- CCG品牌论坛
- 中国与全球化论坛
- 学术委员会专家
- 主席/理事长
- 中文图书
- 品牌论坛
- 研究合作
- 重点支持智库研究与活动项目
- 概况视频
- 主任
- 香港委员会名誉主席
- 关于
- 团队
- 国际关系
- 国际组织
- 加拿大
- 华人华侨
- 国际贸易
- 来华留学
- 区域与城市
- 媒体报道
- 二轨外交
- 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
- 高级研究员
- 资深副主席
- 英文图书
- 圆桌研讨
- 建言献策
- 概况手册
- 副主任
- 理事申请
- 香港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 顾问
- 研究
- 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
- 区域合作
- 欧洲
- 中国海归
- 来华投资
- 出国留学
- 大湾区
- 活动预告
- 名家演讲
- 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
- 特邀高级研究员
- 副主席
- 杂志
- 名家演讲
- 媒体采访
- 年报
- 秘书长
- 企业理事
- 香港委员会主席
- 国际顾问
- 国际贸易与投资
- 一带一路
- 亚洲
- 留学生
- 对外投资
- 国际学校
- 动态
- 名家午餐会
- 中国人才50人论坛
- 特邀研究员
- 理事长
- 媒体采访
- 文章投稿
- 副秘书长
- 活动支持
- 香港委员会副主席
- 国际教育
- 非洲
- 数字贸易
- 活动
- 智库圆桌会
- 常务理事
- 智库访谈
- 国际合作
- 总监
- 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
- 研究员
- 研究支持
- 香港委员会常务理事
- 国内政策
- 拉美
- 专家
- 理事
- 直播
- 捐赠支持
- 主管
- 中国国际教育论坛
- 个人捐赠
- 前瞻研究
- 澳洲
- 咨询委员会
- 企业理事
- 其他
- 捐赠联系
- 中东
- 成为理事
- 研究报告
- 建言献策
- 出版物
- 理事申请联系
- 智库研究
- 音视频专区
- 联系我们
- 观点
- 捐赠
- 工作机会
- 香港委员会
-

何伟文:什么才能叫中美新型经贸关系
专家简介
2015年10月8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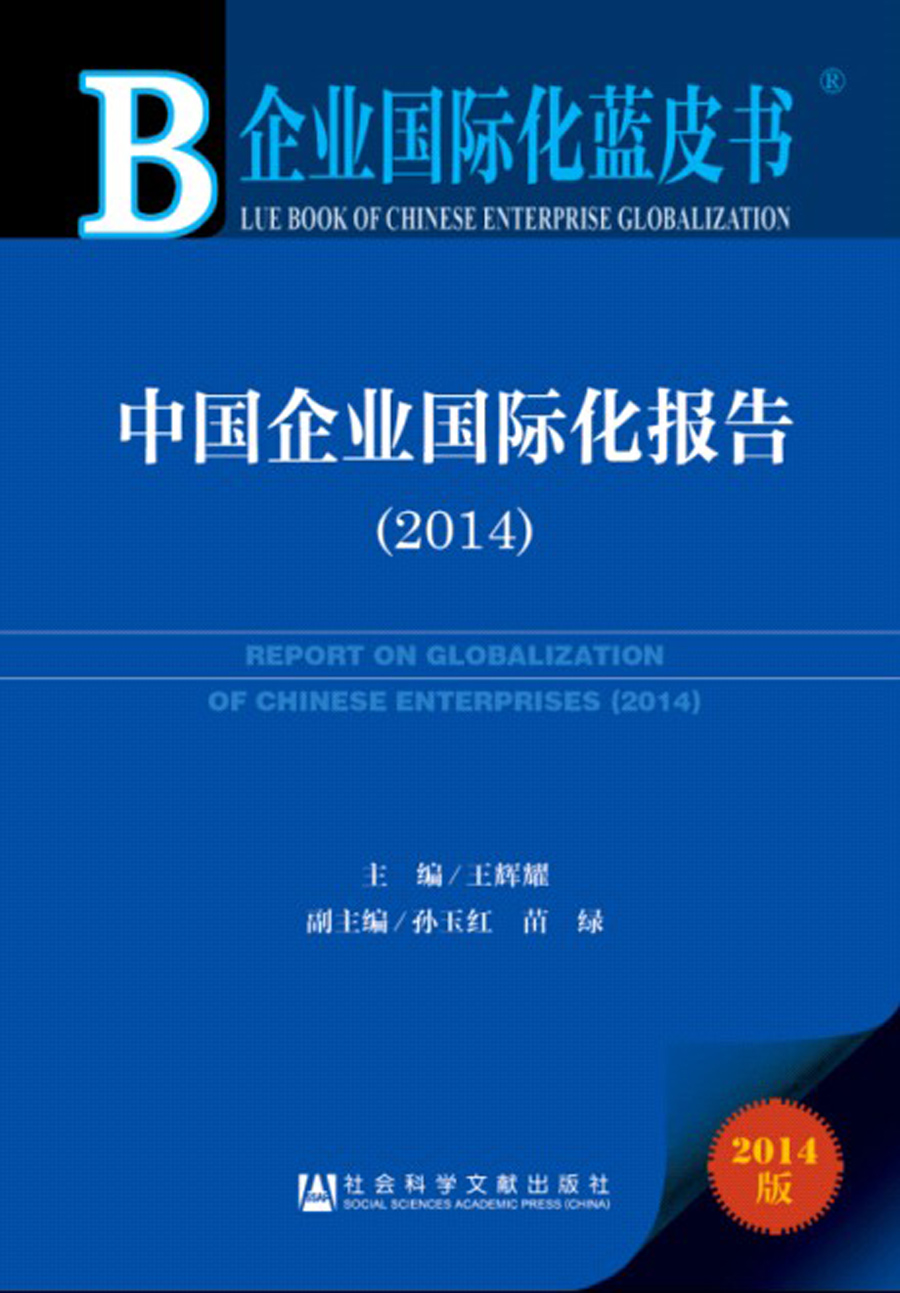
【企业国际化】赴美投资?了解这些很重要
摘要
2015年9月17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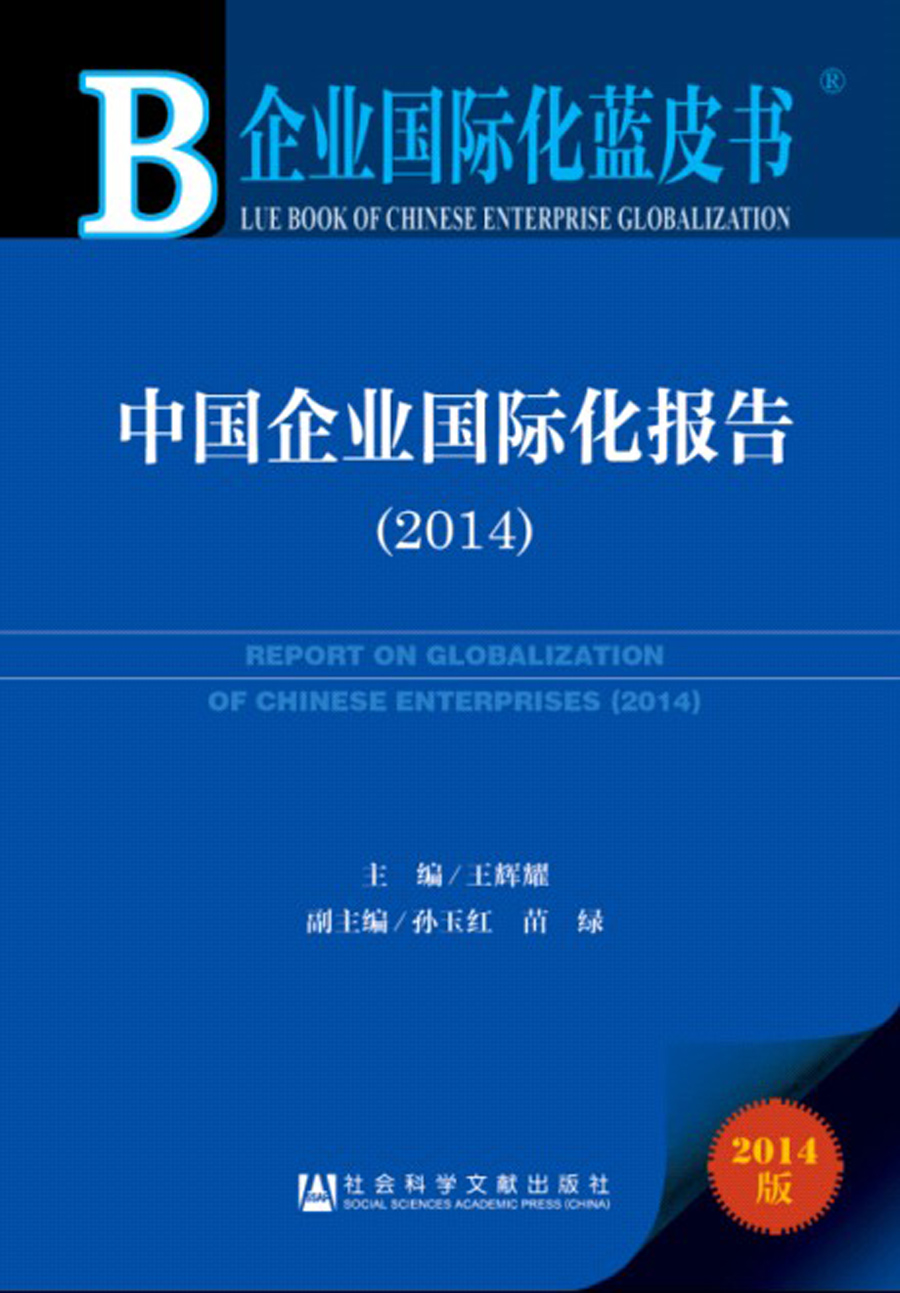
【企业全球化】善用“软实力”,减少“杀伤力”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孙玉红
2015年9月10日 -

汤敏:跨境电商改变制造业发展模式
汤敏,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CCG副主任
2015年8月28日 -

打“擦边球”的海外淘金时代,正在结束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储殷 近日来,缅甸政府对百余名中国伐木工人判处重刑,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尽管这一判决明显偏重,且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但其中透露出的中国企业与个人在海外拓展时的法律风险,却值得重视。 海外利益的拓展有两个基本的模式:一为国企模式,一为民企与私人模式。 一方面,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推进的海外投资,大都集中在资源、基建、能源等领域,而这些行业往往涉及高度政治性的国家战略选择。因此,“上层路线”往往是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相对而言,所在国的法律往往是项目执行的细节问题,尤其是当所在国司法独立性与法治环境较差的时候,法律上的考量往往让步于政治上的博弈。 另一方面,以民企与大量海外淘金人员为主的“走出去”,又往往缺乏专业的法律方面的培训与协助。他们通常带着某些国内长期养成的习惯,以想办法而非走法律的方式来打开局面。有的时候,在一些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与地区,这种“想办法”甚至演变成为了对当地基层执法机构与人员的贿赂。 坦率而言,这两种现象的出现,并不能完全归咎于中国企业与人员的法律意识淡薄,而是所在国法治环境恶劣倒逼出来的结果。因为在很多时候,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讲法律反而寸步难行。比如,在中亚一些国家,中方人员的劳工签证就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往往采矿权办下来之后,中方人员因迟迟拿不到劳工签证而难以入境。在很多时候,甚至包括国企在内,要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安排人员持商务签证入境,“非法”打工。当地警察深谙中国企业这一困境,往往趁机骚扰中国企业与工人,进行罚款甚至索贿。久而久之,甚至形成了不成文的灰色规则,一些中国企业甚至将这种罚款与贿赂,视为正常的经营成本。又比如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中央政府权威薄弱,地方政府甚至武装力量直接控制着当地的资源,要想走进去就必须获得当地部落而非获得中央政府的许可。这次缅甸的非法伐木事件,中国工人并非无证盗伐,只是办的是克钦族武装的许可证而非缅甸政府的许可证。 随着中国走出去的企业与个人越来越多,这种规避法律、变通权宜的办法,已经越来越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一方面是因为走出去的企业和人员太多,让原先规模不大的灰色交易迅速扩大,从而引起当地社会的强烈反弹。另一方面,因为中国企业与人员快速发家致富,激起了当地一些权势集团的觊觎之心,进而以“翻脸执法”的方式,掠夺中方企业与个人的财富。比如,在非洲一些国家已经发生对中方企业、人员大规模的驱逐。 在近几年的海外利益输出中,由于漠视法律而遭遇的风险,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海外企业(个人)所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一带一路”上的一些不发达国家与地区,当地的政府与社会对于企业合法经营的关注度也已经越来越高。小聪明可能带来大麻烦,甚至变成大风险。必须意识到,靠着打“擦边球”获利的海外淘金时代,正在走向终结。 本文刊于《中国青年报》第2版,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8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