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

【参考消息网】中国智库全球排名升至第二位 仅次于美国
核心提示 在亚洲智库60强中,中国有18家智库上榜。在最佳政府智库75强中,中国有6家上榜,其中5家名列前20名。全球最值得关注的智库100强中,中国有5家上榜。 参考消息网2月10日报道 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1月25日在京发布。该报告显示,中国拥有智库435家,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 根据报告,美国拥有1835家智库,保持智库数量世界第一;中国拥有智库435家,稳居世界第二;英国和印度的智库数量位列中国之后,分别为288家和280家。根据区域分布、研究领域、特殊成就三类标准,报告共列出52个分项表单。其中,中国智库上榜的表单数达到41个,与2015年相比增加了13个,反映出中国智库的良好发展态势。 综合排名榜单175强中,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蝉联榜单首位。排名第二的是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该机构同时还被评为年度智库。中国有9家智库入选,包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等。 在亚洲智库60强中,中国有18家智库上榜。在最佳政府智库75强中,中国有6家上榜,其中5家名列前20名。全球最值得关注的智库100强中,中国有5家上榜。 另外,智库榜单也是世界政治经济实力版图的反映。美国以总计1835家智库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智囊资本,也即拥有了最强大的“软实力”。中国、英国、印度、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大国的智库也名列前茅。而西亚和北非地区总共只有398家智库,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总共只有615家智库。 该报告由詹姆斯·麦甘博士领衔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项目团队撰写,今年已是连续第十年为全球智库进行综合评价,在全球60多个国家的86个城市同时发布,是国际上一年一度最权威和最有影响力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年,项目团队从6846家被提名智库中遴选出了175家进行全球顶级智库排名。评分标准参考了4750名新闻记者、政策制定者以及各领域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章选自参考消息网,2017年02月10日
2017年2月13日 -

【亚太日报网】CCG智库建议:中国可考虑加入TPP
2017年2月9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发布题为《中国外交进入新方位,可考虑加入TPP》的研究报告,报告分析了特朗普执政后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指出在中国外交进入新方位的历史时点,加入TPP可以成为中国当前经济外交的重要抓手。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1月20日执政以来,退出TPP等数个连签的行政命令、几十个国际首脑电话、天天推特制造了眼花缭乱的局面,也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CCG秘书长苗绿博士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为实施经济外交打下了基础,加入TPP可以成为中国当前经济外交的重要抓手,中国应把握时机尽快加入TPP。 《报告》从多个角度分析了中国面临的新挑战和加入TPP对中国外交带来的新机遇: 首先,当前部分TPP成员国积极支持中国加入TPP,主动加入TPP可填补美国退出后的空间,通过经济外交改善国际关系; 其次,中美存在广泛、深厚的共同利益基础,主动加入TPP有利于FTAAP的构建和更全面的区域经济安排; 第三,特朗普向俄罗斯靠拢,有意在东亚等地制造潜在摩擦,主动加入TPP有利于凝聚儒家文化圈,改善与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促进亚洲一体化,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深入实施; 第四,中国角色备受关注和期待,主动加入TPP可以进一步展示中国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世界共同繁荣的决心。 亚太日报此前报道,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曾表示,虽然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两国要挽救此协定,鼓励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加入。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重申中国一直主张建设开放透明和互利共赢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目前形势下,无论发生什么,都应该继续走开放,包容联动的发展道路。”(亚太日报记者 王国涛)文章选自亚太日报网,2017年02月09日
2017年2月13日 -

[East Asia Forum]A time of test for the Chin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The ‘Chin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essentially a story of a hyper-charged economy led by an authoritarian state. But now the model has become unsustainable, with China experiencing economic slowdown as well as rampant corruption, growing inequality and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This is an ideal time for Chinese leaders to move the country’s growth model focus from exports and investment to qualitative internal development. It is also the time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build institutional checks on state authority and boost accountability.If China can complete this transition on both fronts, the China model will stand. But a sustained economic downturn or a lost decade or two could mark the end of the China model.The notion of a China model first emerged in Joshua Cooper Ramo’s 2004 article ‘The Beijing Consensus’, which asserted that China had found a unique path to modernisation through a willingness to innovate, taking account of quality of life and providing enough equality to avoid unrest while refusing to let other Western powers impose their will.The China model notion re-emerged after the successful 2008 Beijing Olympics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which China weathered better than many Western countries. The China model became a popular term in the so-called ‘discourse of greatness’, which included terms like ‘the China miracle’ and ‘the rise of China’. But the Hu Jintao–Wen Jiabao administration avoided endorsing the China model, reflecting a hesitancy to engage in ideological debate and a concern over the emerging perception of the ‘China threat’.The China model has also been a central interest since President Xi Jinping came to office in 2012 and called for a ‘China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Xi’s China model promotes Chinese exceptionalism. According to Xi, because of China’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nly a quintessentially Chinese model can accommodate China’s national circumstances.The key issue in the China model debate is the role of the state, reflecting the long struggle of Chinese elites to build and maintain a powerful state.Since found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as claimed the public mandate by building a centralised state to maintain order. But Deng Xiaoping’s economic reforms in 1979 decentralised many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authorities. These reforms helped China’s economic take-off by creating market based resource reallocation efficiencies.More recently, a neo-authoritarian sentiment has emerged in China criticising the decentralisation of the state authority for weakening central planning bureaucracies and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some intellectuals to advocate liberal ideas from the West.President Xi has echoed this sentiment by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ing state capacity through concentration of personal power, anti-corruption campaigns, empower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launching the largest ideological campaign against ‘Westernisation’ in post-Mao China. Xi has centralised policymaking at the highest levels of the party by moving a large proportion of decision making into small leadership groups. Underlying these moves is a recentralisation of power from Beijing and the CCP to Xi Jinping.Centralisation under Xi has allowed the Chinese state to utilise a much larger economic toolkit than its Western counterparts. China marshalled extraordinary resources into infrastructure, housing and transporta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also much more effective in deploying enormous state capacity to ward off the global recession than its Western counterparts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But this economic growth has come with significant costs, including excessive human casualties, environment pollution and overcapacity as well as income disparity and moral disintegration.These costs have seen China enter a period of deepening social tension, marked by unrest and protests. With China’s economic growth now decelerating, Chinese leaders are increasingly fearful of China descending into chaos. Strikes and labour protests have already increased as bloated private and state-run enterprises lay off millions of workers.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eployed more coercive measures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China’s spending on domestic security outstripped the defence budget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09 and has continued to hit new heights since then, showing the rising costs of maintaining stability. Xi has clamped down on social media, shutting accounts of labour activists, deleting news reports and monitoring chat forums. The state has also prohibited workers from establishing independent labour unions, severely persecuted activists and detained human rights lawyers.As China’s economy slows the costs of the China model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are becoming less and less bearable, even to those who have benefited from its fruits. The existing model does not fit China anymore. This is evidenced by the growing numbers of China’s new rich who are choosing to emigrate abroad and take their money with them. Students are flocking to the West for a liberal college education.The real test for the China model is whether Chinese leaders are able to achieve transformation on both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ronts. China has come a long way since Deng Xiaoping initiated economic reforms in 1978, but now much needs to be done to create a more sustainable China model.About Author Zhao Suisheng is Academic Advisor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the largest independent think tank in China, with over 100 researchers and members of staff.From East Asia Forum,2017-1-29
2017年2月13日 -
王辉耀:选才基数,从“13亿”变“70亿”
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日前,三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允许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在华就业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部分符合条件的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无需工作经历即可在华就业。这是我国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广纳天下英才为我所用的又一举措,是中国实施全球化人才竞争战略的重要一步。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我国逐渐成为国际人才的向往之地,外国人才集聚的态势逐年加强,我国的人才选择从过去13亿人中选才转向今天从全球70亿人中选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研究编撰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4)》中就曾指出,若外籍留学生毕业以后不能直接在我国就业或创业,将在一定程度上屏蔽具有创新创业潜力的外国人才“苗子”,建议顺应世界人才国际化流动的趋势,放开外籍优秀留学生在华就业和创业的限制,我国也可以设置留学生实习签证、工作签证,允许短缺人才或居留达到一定年限、就业创业成绩出色的外国人才留在中国。 继过往两办印发《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安部出台支持北京等地创新发展出入境措施之后,这次三部委联合印发的《通知》对外籍高校毕业生在中国就业应具备的条件、办理程序、有效期、配额管理等做出了详细规定,在此前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并更加具体、务实。用人机构、高等教育机构等各类主体,外国来华留学生、有志来华工作的外籍学生等都将从中受益。 本次《通知》的出台,也加快了外籍人才评价引进机制的市场化探索,更加侧重评价人才实际工作能力及其为用人单位带来的贡献,不再局限于以往国家体制内引进海外人才的诸多条件。这也就赋予了各类用人主体更多的自主权,他们可以根据多层次、多元化的实际用人需要,市场化地选择最适合的人才,极大地便利了企业等用人主体在全球范围内延揽优秀的青年人才,增强了他们选聘国际人才的竞争力。 出国留学与来华留学并重,是留学工作的重要理念,但调研发现,来华留学非常突出的障碍之一就是外籍留学生无法在华实习、就业,无法获得工作、居留的通畅渠道和发展空间,降低了外籍学生来华留学的预期。《通知》的出台,放宽了外籍高校毕业生在华就业的条件,在解决这一问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将使更多有意愿来华留学的外籍学生看到融入的希望,从而积极选择来华留学。这将有助于减少留学赤字,并有助于高等教育国际化和来华留学体系的发展。 人才和创新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目前,制约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走出去”参与全球竞争的因素之一,就是缺乏跨文化的国际人才。吸纳来华留学生和海外高校毕业生在华就业、创业,可以储备和培养更多既有海外背景、又熟悉中国文化、国情的国际人才,促进全球人才环流。同时也向全世界释放了更加积极的信号,欢迎全球人才到更加开放的中国发展,共同实现中国梦。 接下来,我们还需逐步为来华留学生构建“留学—实习—工作—永久居留”的完整链条,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吸引力;同时为全球人才描绘清晰的中国梦蓝图,对优秀人才的认定范围更加开放,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2月9日
2017年2月10日 -

【央广网】为实体经济减负 涉企收费继续“做减法”
央广网北京2月9日消息(记者李硕)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最近,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的一番话受到热议。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宗庆后提到涉企收费负担重,每年企业要交的费用有500多种。尽管事后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对此进行了澄清,说娃哈哈集团最终缴纳的费用只有212项,并没有500项之多,但在经济下行压力犹在的当下,涉企收费较多较重,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强调,要把大力清理和规范涉企收费与深化简政放权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从源头上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国务院部门要带头治“费”,切实起到“以上率下”的作用。 2013年以来,中央层面统一取消、停征、减免涉企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496项,地方取消收费600项以上,2015年以来又出台了一系列减少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和企业社保费用支出的举措。但必须看到,目前收费名目仍然较多、乱收费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加重了企业的负担。 为此,昨天的会议强调,必须尽快推出一批制度性、管长远、见实效的清费举措,加大审计、督查力度,坚决取消事业单位不合理收费,杜绝中介机构利用政府影响违规收费,行业协会商会不得强制企业入会或者违规收费。要抓紧建立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切实减少涉企收费自由裁量权。 就此话题,经济之声专访了会计审计学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张连起。 经济之声:我们说目前收费名目仍然较多、乱收费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这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张连起:“近几年来,减税降费既是振兴实体经济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深化简政放权,推进放管服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目前我们要想优化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要降税减费,特别是减费。 去年以来,一些企业家和学者都针对涉企收费提出了很多观点。企业现在就像‘担担子上山’或者‘下雨天背着稻草走路’——越背越沉。我们看到,这几年各个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2013年以来,中央层面统一取消、停征、减免涉企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496项,地方取消收费600项以上,但是各种名目的乱收费问题仍旧非常突出。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行政性收费;第二是中央层面的政府性基金;第三个就是红顶中介或者权力中介。 可以说,这些费用给企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像残障基金、绿化费以及水利基金等,都是中央各个部门设置的,主要原因就是原来我们国家的企业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当税收无法保障一些公共项目或者公共服务时,我们就以费的形式,也就是‘准税收’的方式收费,这给企业加了担子。” 经济之声:从当前看,为什么大力清理和规范涉企收费如此紧迫? 张连起:“国际上有一个‘拉弗曲线’,一般情况下,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导致税基减小,使得政府的税收减少;当税费负担达到了一定程度,降税反而能带来税源。因此我们要让企业放水养鱼,固本培元,增加其内生动力,否则企业本来就处在盈亏的临界点上,一旦费用增加,它就更加难以存活了。 现在,除了制度性交易成本,还有税费成本、土地成本、用人用工成本以及物流成本等,这些综合成本本来就在不断增加,如果涉企收费不加紧‘做减法’,实体经济的压力就必然越来越大。而如果实体经济不再具备国际竞争力,中国经济就很难有国际竞争力。” 经济之声: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尽快推出一批制度性、管长远、见实效的清费举措。下一步涉企收费“做减法”该怎么做? 张连起:“我建议我们在现有的基础上下大力气,砍掉50%到60%甚至60%以上的涉企收费。现在,中央级的行政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录有215项,这其中有绿化的,也有水利的,还有电价的。以电价为例,为什么我们的电价比较高?因为电价里有很多这样的基金,例如:国家重大水利建设基金、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植基金、小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植基金,还有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等。 在各地,地方政府也有它自己的理由来进行涉企收费,一个县公开的收费目录清单就有32项,而且大部分都涉企收费,这样,企业负担重是必然的。建立收费清单制度只是一个工具性的支持措施,我们更多的是要从源头出发,不要设立这么多的收费项目。 减税降费的关键在于要推出能感知、有温度的财税改革,让企业真正感觉到各种名目的收费在明显减少,让企业和群众感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只有给企业添活力,让企业有内生动力,才能涵养税源、扩大税基,才能为企业带来可持续的财政收入。因此要把减税降费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高度,放在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和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高度来进行,只有这样,减税降费的各项措施才能‘落地生根’。”文章选自央广网,2017年2月9日
2017年2月10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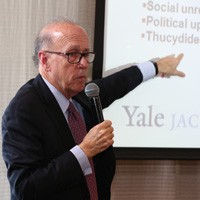
CCG举办月度午餐会 耶鲁大学教授Stephen Roach 讲述“没有中国的世界”
2016年12月14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柏悦酒店举办午餐会。耶鲁大学教授、前Morgan Stanley首席经济学家、亚洲区主席Stephen Roach发表以“没有中国的世界”为题的主旨演讲。 午餐会由CCG秘书长苗绿博士主持。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发表欢迎致辞。CCG高级顾问、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原驻美公使何宁,CCG副主任、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CCG高级研究员、前商务部欧洲司司长孙永福,耶鲁大学商学院教授James Levinsohn,CCG副主席、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汪潮涌,CCG副主席、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王俊峰,CCG常务理事、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中国区总裁陈新华,CCG常务理事、远毅投资合伙人高毅,美林(亚太)有限公司中国业务部董事总经理刘瑾,SK中国区副总裁刘智平,高礼研究院执行院长卢斌,CCG理事、我爱卡/信用宝创始人兼CEO涂志云,CCG理事、富爱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唐浩轩,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卫东,CCG常务理事、华也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CEO叶雪泥,CCG常务理事、香港铁路有限公司首席顾问-中国业务易珉,塔塔集团中国区总裁詹宏钰,CCG常务理事、金山软件CEO,执行董事&金山云CEO张宏江等嘉宾与会等各界精英人士出席午餐会。 CCG理事长王辉耀博士在表达了对耶鲁大学教授、前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首席经济学家、亚洲区主席Stephen Roach、耶鲁大学知名教授 James Levinsohn以及CCG理事和各界的精英人士的热烈欢迎之后,表示世界经济和全球化已发展到了一个转折时期,欧洲、美洲正在经历一系列的前所未有的变革,中国则在推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愈发关键的角色。全球已经走向融合,贸易战无益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未来中美两国的大方向是共存合作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形成健康的中美关系,无论对于两国之间还是世界各国都会大有裨益。 Stephen Roach教授在演讲中指出,特朗普的经济战略存在巨大缺陷。多边问题是无法通过双边方法解决的。中国是美国逆差中最大的国家,但美国与另外近百个国家都是赤字。如果只将重点放在中国或墨西哥等产生“赤字”的国家,不从中国进口,施行保护主义,无益于美国持续的经济增长,也无法根本解决储蓄短缺等美国自身内部存在的问题,美国人承担的成本会大幅度提高。世界不能没有中国,否则世界经济难以保持持续增长。在即将到来的负储蓄时代,美国将越来越依赖来自海外的储蓄盈余,中国无疑可以提供大量的支持。所以,很明显“特朗普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美国经济的复兴,未来需要做出改变。 随后,与会学者、企业家就当今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进行了热烈研讨。 何亚非在总结发言中表示,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成为了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驱动力。另外,中国开始逐渐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重要一环。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今年中国杭州举办G20领导人峰会,逐渐展现出了自己的领导能力。现在世界局势风云变化,“特朗普风暴”已经波及到了欧洲。但是中国在稳定自由贸易、气候变化、经济复苏等方面依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何亚非对于中国和全球化的未来持乐观态度,他指出,历史让我们更加坚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随着“一带一路”的提出,必将形成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合作共赢的局面。全球化的大方向不会改变,我们应该准备好,随时应对新的条约和规则。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尽管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但是,事实上,若没有中国经济的长足驱动,世界经济早已陷入衰退。出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担忧,有必要审视中国的全面危机。此外,美国大选结束,“特朗普经济”对中国及中美经济关系的影响也在研究之列。午餐会旨在探寻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为中国经济作做出建设性的政策总结及建议。
2017年2月10日 -
张蕴岭:创新、活力、联动、包容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关键点
张蕴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1月的预测,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为3.1%。世界银行2017年1月的预测更低,仅为2.3%。这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最低增长速度。它表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阴影仍未散去,世界经济结构性调整的长进程仍未到头。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应把握好创新、活力、联动、包容这四个关键点。 世界经济仍未走出危机阴影 发达国家经济低速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发达经济体2016年整体经济增速为1.6%,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0%。其中,美国经济曾出现短暂的较快复苏,但很快又陷入乏力。因此,美联储长时间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直到2016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才出现明显提升,增长率达到3.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均预测美国2016年经济增长率为1.6%。欧元区经济受欧元危机和英国脱欧的双重影响,缺乏增长的内在动力。尽管欧盟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增长的势头仍然较弱,预计2016年增长率为1.7%。日本政府采取了较大力度的宽松货币政策,2016年第三季度经济出现好转,但难有大的起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其年增长率只能达到0.9%左右。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体上面临发展困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临外部需求降低、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下降和外资流入减少等困境,经济增长率放缓,预计2016年整体维持在4.1%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增长速度是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普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实现的,增发的货币没有导致商品价格上涨,劳动生产率没有明显改观,新的经济增长结构还没有形成。在新兴经济体中,有些国家经济继续负增长,如巴西、俄罗斯。印度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但速度放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其2016年增长6.6%,比2015年下降1个百分点,低于中国的增长速度,主要原因是消费下降。印度经济总量较小,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相比之下,中国经济成为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顶梁柱。尽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换挡,实际增长速度为6.7%,但由于经济总量大(2015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为17.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40%。 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放慢,逆经济全球化势力兴起。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较长时间里,随着国际生产分工深化与扩大,大量投资流向新兴经济体,新的加工出口中心形成,大量的中间产品在不同生产环节快速交换流转,终端产品的进出口爆发式增长,使得国际贸易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很多年份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成倍于世界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但危机爆发后,国际贸易和投资一直慢于整体经济的增长,原来的贸易增长快车遽然失速。此外,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了逆经济全球化的动向。比如,西方国家主张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总统选举中胜出;推动世界市场开放的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谈判多年停滞,已经达成的多边便利化协议难以落实;赢得大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坚持“美国第一”,对外国产品征收高关税;一些国家对进口和外来投资实施的限制性条款、临时措施、特别审查不断增多;等等。逆经济全球化势力得到少数拥有巨额财富的既得利益者支持,他们想要借此来维持财富分配的不平衡态势。这会造成世界经济发展更加不可持续。 世界经济出现低利率、低投资、低通胀和低增长并存的局面。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些“悖论”。比如,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导致商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率处在低水平。日本、欧元区都实行了量化宽松政策,但通胀率都很低;美国通货膨胀率水平相对高一些,但也低于预期。再比如,低利率一般有助于促进企业投资,但在各国几乎都采取了低利率政策后,投资的增长仍然缓慢。从整个世界看,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国际贸易增长和经济增长的速度,特别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下降更多。世界经济中这种低利率、低投资、低通胀和低增长并存的局面隐含着诸多复杂矛盾。这些情况表明,世界经济还处在结构调整的进程中,新的平衡远没有形成。 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 总的来看,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世界经济发展仍然存在制约复苏的结构性障碍,加上一些不确定因素,使得世界经济仍将呈现较长时间的平淡状态。推动经济增长仍然是各国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各国还会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特别令人关注的是美国的政策走向及其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市场越发敏感,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让美元汇率升高,导致资金向美国流动,这对其他国家的投资造成不利影响。如果美国政府大力减税、大幅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积极鼓励美国公司生产回归,美国经济增长可能会有明显提升。但美国这样强力推行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必然会引起许多新的矛盾,为世界市场增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导致稍有好转的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又被削弱。 预计2017年的世界经济形势将比2016年有所好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7年世界经济增速为3.4%,世界银行最新预测为2.7%。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会略有提升,但对拉动世界经济的贡献仍然较小。其中,美国经济在“特朗普新政”的刺激下可能会略有起色;欧元区经济由于市场信心下降等影响,不会明显好转;日本安倍政府“三支箭”都已射出,货币政策几乎用尽,经济将继续低迷。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预计将提升到4.5%,其中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是一个重要因素。印度经济将继续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东盟国家的经济将有比较明显的改善,拉美国家可能会从负增长转为正增长。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会有所上升,巴西、俄罗斯经济有望一改收缩局面,出现正增长。随着世界经济总体形势好转,预计国际贸易形势也会有所好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7年国际贸易增速可能会达到3.8%,由此扭转连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的状况。 近20年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迅速提升,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动力与活力的重要源泉。当前,尽管发展中国家经济正在经历艰难调整,但总体而言,它们的增长速度仍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特别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2016年的经济增速是世界经济增速的2倍多、发达国家整体经济增速的4倍多,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 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为尽快走出低增长、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努力。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世界经济开出了一剂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药方。 向创新要动力。从根本上说,这次危机经历如此长时间的调整,主要是因为新旧增长动能还在转换中。科技进步、人口增长、经济全球化等过去数十年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先后进入换挡期,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提供的动能消退,新一轮增长动能尚在孕育。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世界经济缺乏较强的增长动力。要想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唯有把握创新、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的历史性机遇,向创新要动力、向改革要活力。这是国际社会形成的一个共识。新技术发展推动新一轮产业革命蓄势待发,这一方面会创造大量富有活力的新经济形态,另一方面会推动生产率大幅提升。当今技术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新技术的扩散性比以往强得多,不仅仅局限在发达国家,也会很快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扩散,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链。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提出世界需要创新增长方式、通过《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制定《2016年二十国集团创新行动计划》等,都是推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阴影的关键举措。 顺应开放的大趋势。新技术的发展必然会让世界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国际生产分工将越来越深化,企业的经营将越来越以世界市场为依托。拿美国来说,在采取吸引本国企业回国生产的措施后,会出现一些企业的部分生产回到本土。但企业大规模回流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它们难以在本国建立完整的生产供应链,即使建立了也会使自己的产品失去国际竞争力。因此,世界市场开放是一个大趋势,市场开放必然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对一国来说,开放是必然选择;以邻为壑不仅无法摆脱自身危机和衰退,而且会压缩经济发展空间。然而,仅仅靠市场开放并不能解决经济发展的所有问题。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少还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各国制定协调、平衡的经济社会政策;二是改善综合环境特别是提升基础设施与人的能力,促进世界市场有序和渐进开放。 协调各国经济政策。在国际经贸合作方面,发达国家致力于推动建立新的高标准经贸规则,发展中国家则关注综合发展环境的构建。世界经济要行稳致远,既应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又应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提出世界经济联动与包容式发展。联动意在实现各国经济政策上的协调,维护开放与合作的大环境,实现共同发展;包容意在让各方都有参与和发展机会,缩小发展差距,促进收入和财富分配公平,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世界人民。这样,世界经济才更可持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说,以往的经济增长只惠及了少部分人,经济全球化必须有所改变,不能再像过去所看到的那样,增长主要由贸易来推动,而是要考虑到包容性。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联动与包容式发展的范例,它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与沿线各国和地区发展规划和需要对接,通过基础设施、开放的产业园建设等改善当地的经济发展环境,构建开放合作的新型框架。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2月9日
2017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