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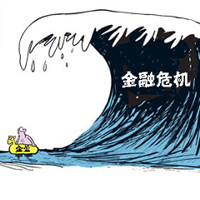
【新浪财经】人民币或将成为国际避险货币
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梁海明如果未来两三年内爆发环球金融危机,笔者认为,届时“一带一路”将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必需,人民币也很可能将成为国际避险货币之一。 环球很快将爆发金融危机?笔者近日在澳大利亚出席国际金融技术分析师协会(IFTA)年会时,与一些参会金融分析师交流,许多人从不同类别投资品走势的技术分析中,都读出了波动加剧的意味。对此,笔者认为分析师的看法并非耸人听闻,其实有一定根据,也开始出现一些征兆。 根据彭博社的分析显示,环球金融市场容易“逢七必灾”,例如,1987年10月19日当天纽约股市下跌幅度创史上第二大跌幅,香港股市当天也下跌超过10%,两大国际金融中心爆发小股灾。到了1997年,“逢七必灾”的情况更严重,当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到了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引发记忆犹新的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海啸。 那么,很快就到2017年,“逢七必灾”的魔咒会否出现?如果出现,将会是由哪个国家或者那个区域引爆呢?不少参加国际金融技术分析师协会(IFTA)年会的金融分析师对于这一点则众说纷纭,没有准确答案。 在会上,笔者也表示认同未来两三年内或将爆发环球金融危机的说法。笔者此前曾在多个公开场合指出,在2008年爆发环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金融市场立陷困境,为挽狂澜于既倒,美国推出的量化宽松政策(QE),该政策其后引发多国央行跟随,令全球各地金融系统各方面都高度同质化,这种同质化实际上是扩大了风险的关联性,从而增大了整体脆弱性。如果多数金融机构共同的风险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话,整个金融系统都会受到感染,从而引发新一轮的环球金融危机。 除了上述因素有可能引发下轮环球金融危机之外,笔者相信至少还有以下几个因素或将引爆环球金融危机。 其一,欧洲多家银行接连陷入财困,易引爆金融危机。 虽然环球银行体系看起来较上几次金融危机时更为健全,但实质未然,近期除了德国最大市值的上市银行德意志银行深陷巨额亏损、股价下跌、市值缩水等的危机之外,身为欧洲第三大经济体的意大利,该国金融业的不良贷款比率高达18.1%,不但远超5.7%的全欧元区平均值,且该国这一比率更是美国的10倍,即使在2008年爆发环球危机之时,美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仅有5%。 屋漏偏逢连夜雨,意大利银行的3600亿欧元不良贷款中,除了2100亿欧元确定打入坏帐之外,近年欧洲央行的负利率政策,对意大利银行业获利能力已是一次重击,更加深其困境。而英国脱欧普遍加重了欧洲银行的压力,欧洲央行将把低利率维持更久,以此希望力阻英国脱欧对欧元区的冲击,这很可能引爆意大利银行全面危机,进而容易引发欧洲乃至环球金融危机。 在国际金融技术分析师年会上,欧洲也是大多数分析师感到不确定性和市场波动性最为巨大的地区。 其二,全球债务过度膨胀,存在爆发危机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字显示,全球债务水平已亮起了红灯,截至2015年底全球债务高达152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总规模的225%,当中1/3是公共债务,占全球GDP总规模的85%。加上目前在各国央行只有更宽松,没有最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环球金融市场充斥大量廉价资金,触发全球企业大举借“便宜钱”,有国际评级机构估计,全球企业债务规模有可能由当前的逾50万亿美元增至数年后的75万亿美元。 在这种全球杠杆化、泡沫化之下,一旦未来几年利率回升上涨、经济持续萎靡不振,将极大增加企业的偿债压力,若届时企业偿债能力出现问题,且银行收紧信贷,将引发企业破产潮,银行亦将遭受重击,随之引爆环球新一轮金融危机。 其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增大了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 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加剧了大宗商品生产国的财政困难,如原油价格近期虽有回升,但仍是从最高点下跌了约70%至80%,不少原油出口国出口收入大幅下滑,但财政支出却难削减,导致财政赤字愈来愈高,若包括原油价格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容易引爆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进而引发金融危机。 而且,大宗商品价格长期低迷,扩大了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经常账户逆差,而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扩大,将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带来贬值压力,部分大宗商品出口国的货币这两年来已贬值超过30%,部分贬值接近60%。由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正是由亚洲货币贬值从而演变成爆发金融危机,现今如多国货币汇率持续贬值,也将容易引发一场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 如果未来两三年内爆发环球金融危机,笔者认为,届时“一带一路”将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必需,人民币也很可能将成为国际避险货币之一。 这是因为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实质是有助于扩大全球总需求,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不但是中国与各国双边合作模式的新突破,也是国际经济合作模式的新探索。 若环球金融危机爆发,重创环球经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提倡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与欧美多国优势互补,进行联合体投标、联合生产以及联合投资等新型合作,在尊重第三方国家意愿的前提下,实现三方互利共赢,此举有利于稳定环球经济。 与中国相比,欧美多国在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殖民地时代的历史渊源,欧美国家对当地了解甚深、人脉丰富且有丰富运营、管理的经营,加上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合作”有利于分摊投资风险,以及减少中国与欧美国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独立投资时可能出现的对抗,增加对冲、合作的空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对于新兴国家而言, “一带一路”将为新兴国家带来更多的投资资金,更多的商贸合作项目,与新兴国家共同分享相关商机,这不但会为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助力,更将共同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体系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对于工业化程度相对不高,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仍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政策、资金、贸易、设施和民心等五个领域加强互联互通,为他们提供技术、资金,以提升其技术和工业化水平,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整体的发展。 因此,若爆发环球金融危机,“一带一路”倡议更彰显其作为环球经济促进器、推动器的作用,不但能够创造出友善的国际环境,也能完善和推动国际经济治理改革,与世界各国携手维护及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 另一方面,环球若爆发金融危机,人民币很有可能将成为国际避险货币。2008年爆发环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对美元价值及由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质疑声不绝,美国政府有关“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麻烦”的做法,令国际市场上有不少声音希望改变美元拥有“嚣张特权”这一国际货币秩序。而且,各国也希望避免采用美元作为主要结算货币,而必须承担汇率波动风险、信用风险、贬值风险和要承受因美国转嫁金融危机而殃及本国经济金融体系等的风险。 但是,由于欧元、英镑及日元因为所在区域、国家经济增长乏力,汇率也显著波动,可供国际社会选择的国际货币并不多,已经正式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特别提款权)篮子内的人民币,将成为一个新选择。 而通过扩大、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流通和地位,既可增加安全的国际储备资产的供应和选择范围,降低对美元这一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依赖性,又能减少美元汇率波动对国际市场所带来的冲击。因此,而一旦爆发环球金融危机,有可能更加吸引各国将人民币作为避险货币,从而增持人民币,甚至还会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以人民币作为标价和结算货币的可能性,这无疑将提升人民币的汇率,扭转人民币近期持续贬值的态势。 环球若爆发金融危机,会否真如笔者所言,可大幅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汇率呢?拭目以待!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6年10月31日
2016年11月1日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Is it time for China to Open its doors to Filipino domestic helpers?
China’s growing demand for skilled domestic helpers offers the prospect of a new line of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as the two countries try to mend ties by playing down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While China has a particularly strict work visa system for foreigners wanting to work legally on the mainland, an estimated 200,000 Filipino domestic helpers are working there illegally. Philippine labour minister Silvestre Bello said last month that Beijing should legalise their stay and that he would raise the issue with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Bello said earlier this month that he would also urge Philippine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to discuss the issue of “undocumented” Filipino domestic helpers in China with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Duterte is likely to raise the issue during his visit to Beijing this week, according to the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newspaper.While there are 20 million domestic helpers in China, there’s still a huge shortage of supply,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Most domestic helpers in China are middle-aged female rural migrant workers known as ayi (aunt), with little training or education.Meanwhile, China has kept the door shut to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In July last year, Shanghai began allowing foreign residents to legally hire domestic helpers from overseas. But Chinese citizens are not permitted to employ them, and reports said only five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had been granted approval to work in Shanghai by the end of last year.Growing weary of hiring and firing Chinese domestic helpers who were poorly educated and ill-mannered maids, Shanghai advertising agency boss Shirley Yang said it was only natural that she began thinking two years ago about finding a Filipino domestic helper to take care of her twin babies.“I had been using a mainland maid for some years,” she said. “They are from rural areas and have little education. What’s more, they have inappropriate manners, such as spiting on the ground while going outside and making noises while drinking soup.”When she visited an American colleague’s home and saw their Filipino domestic helper looking after the house in a more professional way, she was impressed. After contacting employment agencies and scouring classified websites, she finally hired one herself.“The Filipino ayi is much better than the Chinese one,” Yang said. “She really tidies up my house, mopping the floor every day and folds clothes neatly. She also likes playing with my kids. She also teaches them to learn do things by themselves” – a quality her Chinese predecessor lacked.The commerce ministry report said the salaries of domestic helpers were rising rapidly in Chinese cities, especially for yuesao – nannies able to care for newborn babies. The monthly salary for a yuesao in Shanghai surged 27 per cent to 10,532 yuan (HK$12,126) in 2014.That makes Filipino domestic helpers, also popular in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Canada, even more competitive in Chinese cities, in addition to their professionalism and English-speaking abilities.In big Chinese cities, a Filipino maid has become the very marketable asset for employment agencies. In Shanghai they can earn a 40,000 yuan commission when a client signs a three-year contract for a Filipino domestic helper. The salary is 7,000 to 8,000 yuan a month, which even at the lower rate is close to double the HK$4,210 minimum domestic helper salary in Hong Kong.Without work permits, most Filipino domestic helpers enter the mainland on tourist visas that allow a stay of up to 14 days. After two weeks, those who stay illegally have to pay a fine when they leave the country.“The mainland border control authority will fine them for overstaying, but the fines are often paid by us, the agencies,” a staff member at Guangzhou-based agency Maid Boss said.Staying on the mainland illegally can, however, make overseas domestic helpers vulnerable to abuse and mistreatment. The Guangzhou employment agent, for instance, said she usually told Chinese clients “to take away the passports of Filipino workers” so that they could not “run away”, and she often told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working illegally on the mainland “not to talk to strangers”.By skirting mainland regulations and visa rules, she said she had introduced more than 10 Filipino domestic helpers to Chinese families in Guangzhou, Fuzhou, Hangzhou, Shanghai and Shenzhen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Some employers register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as office employees so that they can get work visas. Yang registered her Filipino domestic helper as an employee of her advertising agency.Domestic helpers from the Philippines, and increasingly Indonesia and Myanmar, comprise one group of foreigners working illegally working on the mainland. Others include factory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from Vietnam and Myanmar and merchants from Africa.Despite having an increasingly rich and elderly population and a looming labour shortage, China remains determined to keep “low-end” foreign jobseekers out of the country. In big cities, up to half of the demand for domestic helpers cannot be met during the annual Lunar New Year holidays, according to a government report.Xue Shuai, the founder of yunjiazheng.com, a website matching domestic helper supply and demand, said legalisation of Filipino domestic helpers would not have any impact on the market.“It will be like a drop in the sea,” Xue said.Meanwhile, although China has never publicly admitted it, it seems Beijing has been using visa controls on Filipino workers to put pressure on Manila, according to employment agents.Tim Chen, who owns an employment agency in a southeastern coastal city on the mainland, said China had tightened visa controls when the Philippines took China to an international tribunal over their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ith the pressure ramped up this summer when the tribunal in The Hague ruled against China.So, if the domestic helper issue can be part of solving the Beijing-Manila puzzle, Duterte could bring it to the table.Miao Lu,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Beijing-based Centre for China and Globalisation ( CCG) think tank, said China could treat Filipino domestic helpers as “licensed technicians” to open the door.“It’s likely Beijing will give the nod to the Philippines’ proposal to allow its domestic helpers to work in China legally because ... China is in badly need of such workers,” Miao said. (By Alice Yan)Fro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 October, 2016
2016年11月1日 -
专访丨共享国际人才红利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
中国必须建立更加开放的人才制度体系,充分挖掘、利用国际国内人才红利,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世界教育信息》:《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扩大人才开放。树立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充分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人才资源,主动参与国际人才竞争,完善更加开放、更加灵活的人才培养、吸引和使用机制,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确保人才引得进、留得住、流得动、用得好。”这里提到了国际人才的问题,您认为国际化的人才对于中国的发展意义何在?王辉耀:当下,全球化已进入第四个浪潮——全球经济治理转型升级的新阶段,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亚太自贸区(FTAAP)、“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二十国集团(G20)等新的国际多边合作机制纷纷出现,并积极向前推进,全球治理面临转型升级。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重要获益者,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并加入新一轮全球化竞争,积极参与制订新的国际规则,内外联动推进中国的改革,维持已经取得的贸易优势,提升资本优势,建立人才优势,在全球治理中占据主动,推动全球化进程。中国不仅是全球化的参与者、受益者,更是主要的推动者,因此需要更多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人才。从经济全球化流动中的企业主体来看,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和价值链重构,引发新的全球商业版图调整。企业要在这一进程中取得国际竞争优势,关键点同样是人才和创新。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商企业,通过互联网技术创新,实现新的商业形态,促进了全球商品流动,极大地改变了原有商业格局。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通讯企业,通过持之以恒地自主研发、科技创新以及本地化运营,真正实现“走出去”“融进去”。这些例子无一不说明人才与科技创新能力在经济全球化流动中的主导力量。随着贸易自由化和资本全球流动给各国带来的红利不再突出,全球人才流动浪潮的作用日趋明显。美国之所以在创新领域走在前面,是因为充分享受了国际人才红利。美国硅谷的繁荣就源于多元化的人才集群效应——世界各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语言背景的人才,相互碰撞思想,没有条条框框,时时刻刻产生新的灵感和思路。以色列是全世界创新创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只有60万人,现在800万人,其中80%以上的人口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这些人才的知识、经验和创新能力为以色列发达的科技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国、以色列等发达国家的例子都充分说明了国际人才竞争的必要性。中国现在也正在进行许多重大项目,如“一带一路”的战略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企业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并且在全球化的市场中开疆拓土。所有这些都需要充足的人才储备——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关键是海外人才布局。应从软环境建设、人才体制机制完善和建立健全人才移民制度、大力引进国外人才三方面应对人才流失的状况《世界教育信息》:改革开放后的移民中,留学人员、知识型人才占了很大比例。目前,高端人才外流趋势仍不容乐观,您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王辉耀:当前“人才战争”硝烟渐起。许多发达国家通过改革移民政策,加大人才吸引或留置力度;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不甘示弱,纷纷加入全球人才竞争行列。近些年,我国在“千人计划”的引领下,已有近百万留学生回流,其中高层次人才两万多名。但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我国的人才流失现象仍然十分严重。第一,从硬件方面说,中国的基础设施环境确实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我国不仅科研设备运行效率较低,而且综合效益也有待提高。科技部前部长徐冠华曾说,我国大型科研设备利用率只有25%,而发达国家是170%。许多留学生曾经反映,他们在国外做实验,即使是研究生阶段,也可以使用价格高昂的先进仪器,而回国之后却发现国内的先进仪器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一年也用不了几次。很多专家花钱买了机器,却不愿意分享,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设备利用率低。这些也是很多理工科留学人员不愿意回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中国的科研硬件环境好了很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减小。在很多大城市,中国的科研基础设施已经较为完备,比如北京中关村,现在已经有16家留学人员创业园区,有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301家。中关村的“车库咖啡”新型创新孵化器,还受到美国媒体关注,《华盛顿邮报》刊文《美国人应该真正害怕中国什么》,其中特别提到“车库咖啡”,说这是中关村的“秘中秘”。这说明我国在创新创业环境的改善和激励上,出现了世界瞩目、世界领先的新方法。事实证明,中关村也确实成为了中国集聚海外人才最多的地方。第二,软环境是造成中国人才流失的根本原因。科研设备运行效率低的问题在深层次上反映了我国科研管理体制方面软环境的问题。从科研上说,我国目前科研管理体制还不太健全,也缺乏人性化。在中国,很多科研人员都把精力放在“拉课题”上,而不重视课题最后的成果,产生许多无用的、应付性的科研成果,导致大量科研经费的浪费。在国外,申请课题很容易,而最后课题结果审核却十分严格。再比如,我国科研人员的薪酬水平仍然较低,而在国外,一个教授几乎可以养活一家人,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一国对人才的重视程度。还有,现在很多科研经费规定只能买大型设备,对科研人员的劳务支出等限制严格,还不太人性化,当然现在这一情况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从教育上说,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能力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课堂所教内容与实践脱节,不少教授也疏于教学,很多学生“有学无识”,学术腐败事件时有发生。少数专家掌握一个领域的话语权,不允许别人挑战权威,这种学术垄断限制了学术自由,不仅制约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也成为中国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另外,我国高校存在“只进不出”的用人制度,大部分岗位都被占用,造成一些留学归国人员难以进入高校任职。我国人才体制机制上在近年出现了很多创新和亮点,比如“千人计划”,已经成功吸引了3000多名高层次人才回国。但是目前还存在不少人才管理和任用方面的政策障碍,比较典型的是人才流动的壁垒过高。首先,户籍问题限制了人才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自由流动,也限制了很多人才能力的发挥。 其次,我国人才在体制内外流动也受到限制,许多留学人员回国后缺乏参政议政的渠道,无法发表自己的意见,还没有职称,在申请科研项目上也遇到阻碍。这种社会地位和待遇的差异,也使很多留学人员不愿意回国。在一些国家,“旋转门”机制保障了人才可以在政府、企业和民间自由流动,人才可以发挥能力的领域很多,可以得到有效的锻炼。此外,中国的出入境手续还十分繁琐。相较之下,外国公民的国际旅行、商务往来,都非常方便。最后,创业环境方面,公平竞争和融资机制还需要完善。第三,我国生态环境亟待改善。多年来,我国高污染、高耗能的粗放型经济方式导致了环境污染问题。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生活环境宜居,对优秀人才很有吸引力。《世界教育信息》:针对您所讲到的人才流失问题,中国需要采取什么具体措施?王辉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到,“留学人员是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并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16字方针,表明中央对留学人员统战工作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这一来自祖国的召唤,在海外留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具体来说,我建议中国从软环境建设、人才体制机制完善和建立健全人才移民制度、大力引进国外人才三个方面遏制人才流失,弥补人才流失带来的危害。第一,在软环境建设方面,我国仍需加大科研投入,完善科研管理体制。进行高等教育改革,遏制学术腐败和学术垄断,营造自由的学术氛围。应建立聘任制的教师用人制度,建立退出机制,将科研教学岗位让给更多有能力的人才,给海外留学人员回国进入高校工作创造机会。应继续完善创新创业环境,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第二,在人才体制机制完善方面,降低人才流动的壁垒,使人才利用效率最大化。要放宽户籍限制,促进人才在不同地区之间合理自由流动,让市场竞争决定人才的区域分布。第三,要促进体制内外的人才流动,建立起我国的“旋转门”机制,为人才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要放宽出入境限制,让人才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形成一个人才有出有进的局面,让更多人才走出去学习锻炼的同时,欢迎他们回国服务和发展,这样才能培养更多的国际化人才,让中国成为国际化中心。第四,建立健全我国的人才移民制度,大力吸引国外人才。我国人才流失造成的危害,可以通过吸引海外人才来中国加以弥补。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许多发达国家都曾经历过人才大量流失的历史阶段,通过移民制度吸引人才是发达国家的通常做法。美国一年发放100万张绿卡,这8万张短期人才签证成功地留住了人才。我国设立绿卡制度10年来,只发了几千张绿卡,这和我国对国际人才的需求极不相称。吸引海外人才的重点在于建立健全人才移民制度。首先,要形成统筹协调的签证制度,简化并完善分类。目前,外国人来中国工作必须办理外国就业证或外国专家证、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以及居留证三个证件。三证分立,程序繁杂。今后,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由一个政府部门统筹协调签证相关事宜,例如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USCIS)、澳大利亚移民和公民部、日本厚生劳动省、韩国就业和劳工部等。同时,对签证类型进行适当完善,使之更有利于高新技术领域人才。其次,要出台更为开放的雇佣外籍高层次人才的制度。目前技术移民以职位和任职单位为门槛,基本将外国科技人才流入的接纳单位限制在国有企事业单位。今后应改为以职业为基础门槛,配以国家急缺人才清单或移民职业申请清单,以及雇主联合申请及担保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作用,并以国际通行的积分制来评估申请人的资格。这样才能促进全球人才的流入,并实质推动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和机构的发展。再次,签发“同胞证”或“华裔卡”。目前,我国有5000万海外华侨,他们是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真正的力量源泉。我国的人才绿卡制度,并没有照顾我国海外族裔人才、我国海外留学人才、外国来华留学人员这三个特殊群体,这不符合国际惯例,更不符合我国国情。向他们签发“同胞证”或“华裔卡”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国家的和平统一以及开创我国外交局势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是贯彻十八大“落实党的侨务政策,支持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关心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与和平统一大业”精神的重要举措。欧美同学会为留学生提供更多支持和帮助,为吸引国际化人才发挥更大作用《世界教育信息》:您除了作为智库的掌门人以外,还兼任国家欧美同学会的副会长,您觉得欧美同学会能够在中国人才领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王辉耀:早在2000年,中央便将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纳入统战工作。2013年,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欧美同学会及广大留学人员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贡献,并要求欧美同学会努力成为留学报国的人才库、建言献策的智囊团和民间外交的生力军。2016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建设的意见》。这是中央首个针对欧美同学会建设专门下发的文件,体现了中央对欧美同学会及留学人员组织建设的高度重视。在扶持海归回国创业方面,欧美同学会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欧美同学会下设15个国别分会、商会、企业家联谊会、社团、建言献策委员会等各种各样的分支平台,每个分支机构都是非常活跃的。最近,欧美同学会又成立了海归创业学院,也在力图打造一个智库联盟。此外,欧美同学会是个很好的综合性网络,大家有共同的经历、背景、文化及语言,留学人员能够找到各自的需要,如人才、资金、团队,甚至人生伴侣,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实现。欧美同学会可以帮助留学生反映各种诉求,比如回国的相关问题,创业面临的困难,待遇、身份和居留证。欧美同学会能够把留学人员的这些诉求与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反映和沟通。落实“十三五”规划对于人才工作的要求,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保证《世界教育信息》:国家在“十三五”时期对人才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请您谈谈体会。王辉耀:2016年3月,全国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本次“十三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首次加入了“创新驱动”,并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提出“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此外,中共中央又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这充分显示出人才工作在“十三五”时期的优先地位。进入“十三五”时期,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对内,我国GDP增速放缓,转型压力增大,需要发展科技创新,带动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动力的经济结构。对外,我国海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来华直接投资,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我国“十三五”时期的人才战略,必将放眼于全球,不仅以人才培养为主线,更要辅助以人才集聚、人才引进等措施,加快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加快建立创新型人才队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保证。分析“十三五”规划纲要,可以看出,此次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的举措,都围绕“创新”这一目标,以人才作为未来五年经济社会转型、实现民族复兴的根基与希望。我认为,此次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的特点还包括如下几点:第一,更强调人才制度创新。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指出,我国要发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此后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国际人才制度改革。以外国人才制度为例,过去的一年,我国的重要改革举措有:2015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2015年6月9日,公安部扩大了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2015年9月1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同时,一些新的、极具创新性的政策,已经开始在全国试点。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发达国家,向外国人才发放工作签证、永久居留证已经成为向移民发放的一种“福利”。上海在2015年5月出台、北京在2016年1月出台的人才新政20条,有很多制度已经与国际接轨了,很有国际竞争力。目前,在上海年薪60万元以上、北京年薪50万元以上即可被认定为人才;外籍博士毕业在京工作连续4年,就可以获得“绿卡”;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允许在北京、上海就业、创业;在外国毕业的外籍学生都可以来北京实习。我国也开始通过签证“绿卡”向外国人发放“福利”。第二,主基调更加开放。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人才观,为我国“十三五”期间的人才政策进一步开放奠定了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及“国际人才”,提出“择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观。我曾经在2014-2015年向中央提交在“十三五”时期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的建议,其中包括扩大外国人才永久居留人群范围、降低“绿卡”门槛、吸引和留住外国留学生、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等建议。“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不仅重提“构建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而且提出培养“有国际视野的党政人才”“完善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扩大来华留学规模”“培养推荐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等。这些新的观点被中央采纳,说明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未来五年内,决心培养国际人才的决心。这些国际化制度的改革,将是“十三五”时期人才制度改革的一大亮点。第三,重视打破人才跨界流动的壁垒。鼓励和支持人才流向西部地区和基层岗位一直是我国人才工作的重要方面。“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提高人才“社会横向和纵向流动性”,保证人才上升通道,形成人才跨行业、跨地域流动自由态势;特别提出促进人才在“不同性质单位”之间流动,人才在体制内外的流动壁垒有望打破。第四,重视“高精尖”人才的推动力和高技能人才的支撑力。“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要“推动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实质上是寄创新驱动发展的最大希望于高层次人才。一方面,高层次人才需要在本土加大培养,同时也需要开发外来智力。目前,我国高层次人才流失问题依然严峻。2014年底,中科大发起的调查显示,36年来,中科大少年班培养的超过202位教授中,有185人仍然留在海外。据2011年美国能源部的调查数据,获得科学与工程类博士学位的学生依然滞留在美国的比例,中国博士毕业生2011年为85%,高居第一,比日本、韩国的滞留率高出一倍多。同时,这部分人才是可以被吸引回国和集聚来华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在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研究数据指出,我国目前共有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400多万人。这部分海外人才大部分为高学历人才,本科以上学历的占80%,硕士以上学历的占44%。如何吸引这些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是我国人才政策面临的重大课题。“十三五”规划中列出6项未来五年将要实施的重大人才工程,其中一项是关于高技能人才的“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2011年7月6日,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是中国第一个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但是出台高技能人才的国家层面的重大项目,在五年规划中是首次提到。高技能人才是我国创新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力量。据麦肯锡的预测,我国技能人才缺口约有2400万。2016年,“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我国人民对消费品质量要求提升,要求增加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商品供应。德国、美国率先引领的工业4.0智能工业时代,个性化、定制化产品将成为未来主要的消费品。目前,我国弘扬的“工匠精神”,实质也是“十三五”时期培养高技能人才、为产业升级提供支撑的理念。采访、整理/郭伟 张力玮 文章选自世界教育信息,2016年10月31日
2016年11月1日 -
金灿荣:中国影响力正持续提高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从当前国际关系角度看,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产品竞争、技术竞争、话语权竞争。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前两个层面的国际竞争力已经大大增强。在产品竞争方面,2009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就已经超过了制造业王国德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的产品门类已经相当丰富并且规模巨大。在技术竞争方面,中国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日渐缩小。从目前情况看,中国国际竞争力较弱的方面主要在话语权上。这样的局面,对中国而言是很不公平的。比如,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很多大宗商品的主要生产国或消费国,但对大宗商品恰恰没有定价权,这导致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这种现象已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改变这种局面,不但对中国有利,对世界经济健康平衡发展也有益。 那么,如何改变这种局面、争取中国应有的话语权呢?一个办法是利用已有国际合作机制与国际社会进行有效对话。2016年中国首次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这对中国而言是一次机遇。在刚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中国作为东道国把“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作为峰会主题,向世界宣示了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许多人认为,这次峰会之后,二十国集团这一国际合作平台所产生的活力和效力能够迈上一个新台阶。二十国集团的发展反映出的当今国际社会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际经济力量分布不断变化。原来世界经济可以说由G7(西方7国集团)主导,1991年时这7个国家的GDP占世界的2/3多,因此G7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很有分量,在当时主导着世界经济话语权。而到2015年,这7个国家的GDP总量占世界一半还不到,下降幅度非常之大。反观同一时期的中国,GDP占世界总额的比重从4%上升到15.5%,其他金砖国家的比重也不断上升。因此,新兴市场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对在世界经济政治方面的发言权有了更大需求。总体看,国际经济政治实力对比由原来的发达国家“一家独大”发展为发达国家力量与新兴市场国家力量趋于均衡的局面。 二是新兴市场国家的战略影响力明显提升。近些年,作为金砖国家的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相互之间展开了一定的合作,其中中国的表现尤为抢眼。比如,原来的“上海五国”发展为“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可见,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不但经济实力增强,政治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 三是世界形势变化必然对国际秩序提出新要求。原来G7是国际经济金融的主要协调平台,这一平台现在显然已经捉襟见肘。由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一起共同组成一个协调平台,是国际社会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大势所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中国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中国坚持的全球治理理念将对世界经济复苏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虽然近来中国经济发展有所放缓,但中国的经济增长仍属强劲。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必然随之提高,在国际经济合作协调机制中的作用肯定会持续增强,开始扮演一个主导性角色。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是对现有国际协调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同时,会积极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理念、中国智慧。文章刊于《人民日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10月31日 -

【侨报网】何亚非: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的焦点就是规则争论
专家简介何亚非,CCG顾问、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中国前G20协调人。 【侨报记者王伶羽采访整理】针对近十几年来全球治理出现的新变化和新发展,何亚非表示,今后几十年,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的焦点就是规则争论。谁对新的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有更大的影响力、有更大的发言权?那么现在是谁在改变或者书写新的国际经济规则呢,其实不是中国,中国是受益者。 当然中国也想改变,我们讲的是完善、改进、改革。比如以美国的TPP 为例,TPP 其实是在改写全球经济贸易体系的新规则,这个新规则不是坏事,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但问题在于它受到了地缘政治的干扰。 有些国家想形成小圈子,他们想自己制定规则,这个目的是要维护整体全球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利益格局,希望重新分配某些领域,不想让中国继续获得更大的利益,我把话说得直一点。这里面有地缘政治的干扰,这就显然不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处理国际关系应该平等化的基本准则。 全球化的进程中有很多负面因素,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以及它代表的民粹主义思潮正在上升,这影响了全球化进程,影响了全球自由贸易和全球投资体系。现在反对自由贸易的并不一定是政府,很多是一些国家的老百姓。因为他们对全球化不是太理解,由于全球的负面因素影响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在中低端的企业的工作受到了影响,他们一定有情绪。 这种逆全球化的情绪,我比较担心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发达国家已形成了势头,而且在政治舞台上已经形成了力量,它在改变政治生态,一旦政治生态改变以后,一定会影响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进程。 我们可以预料,未来十年欧洲激进政党一定会在欧洲某些国家掌握政权,这种进程会对全球化和全球贸易产生影响,我们要考虑这一点,我们要考虑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应该怎么办,这也是历史对中国的考试。(根据何亚非先生在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WTO与全球治理发展新趋势研讨会”上的演讲速记整理)文章选自侨报网,2016年10月26日
2016年10月31日 -

【国际商报】引领全球治理,中国愿做“加法”
当前,全球治理新格局隐现,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引发新的保护主义浪潮,不同形式的区域协定在兴起,英国脱欧等事件折射出内顾倾向抬头,全球化面临新的挑战。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15周年之际,回顾与展望中国加入WTO的成功经验与发展前景,新格局将会给WTO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在当前国际经贸格局下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日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美国著名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在北京联合举行“WTO与全球治理发展新趋势研讨会”,针对上述话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中国入世受益匪浅 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指出,今年是中国加入WTO15周年,同时标志着中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进入全新阶段。中国在过去15年里一直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实现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中国的参与改变了全球治理的格局。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何宁认为,中国是加入WTO的受益者,因此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到未来全球治理的活动中,为自身谋取更大的利益。WTO给中国带来的红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多边合作机制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获得平等的待遇,另一方面是多边规则减少了国内政治对贸易行为的干扰。“15年来,中国遵守WTO规则并从中受益;中国非但不想颠覆现有秩序和规则体系,而且是要成为负责任的建设性成员,全世界应该对此放心。”CCG主席龙永图表示,通过加入WTO,中国向世界表明愿意遵守全球规则,并成为参与者和执行者。 现行国际规则亟须改革 龙永图认为,全球治理主要包括经济、政治、社会运作的全球规则,以及制定和执行这些规则的全球机构和区域机构体系。当前,全球治理须进一步丰富全球规则的内涵,加强制定、执行规则的机构,并对全球规则的实施建立监督机制。然而,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国际电子商务、全球变暖等新领域都在近十几年中才出现,清晰的规则体系并不存在,同时WTO规则在多哈回合以后鲜有进展,因此缺失了许多全球贸易新规则。“目前全球经济治理存在严重缺陷,突出表现在治理的碎片化。”CCG顾问、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表示,以美国制定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等理论来指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已不太管用,而中国的成功治理经验获得各国欢迎,由此形成巨大反差。同时,在全球化进程中负面因素累积,造成逆全球化、民粹主义思潮上升,并在发达国家形成势头,从而影响全球自由贸易和全球投资体系。 CSIS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中国商务与政治经济研究课题主任甘思德亦认为,目前的国际规则呈现出诸多弊端,主张中国与美国合作领导全球经济治理,对当前的游戏规则进行改革。 引领全球治理做“加法” 在日前闭幕的金砖国家首脑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且要为世界和平形成制度性保障,这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就西方社会对中国要在全球治理方面“另起炉灶”的偏见,专家们一致表示,中国将继续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对现存体制的修改和完善是为了更好地体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另起炉灶”。“中国崛起后,在规则问题上应参与做‘加法’,不做‘减法’。”龙永图表示,中国也愿意参与做“加法”,如当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无法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时,中国设立亚投行是在做“加法”。中国和美国在制定全球治理新规则方面,可以合作发挥巨大作用,因为它们分别代表了世界上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诉求。 何亚非表示,作为全球化大国,中国应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倡导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从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中汲取营养,提出中国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的中国方案;坚持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超越地缘政治的狭隘和偏见;更加积极主动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主要国家的默契和协商是全球治理的唯一出路。”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霍建国表示,中国的基本理念是共商共建共享,通过改革兼顾方方面面的利益,并在下一步全球治理上、在某些空白领域提出具体的方案,使这些空白领域形成一些新的突破。同时,进一步探讨详细的治理内容和实施方案,争取发挥中国作用、扩大影响力。 CCG特约高级研究员孙永福亦提出,中国在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中要起到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应该更多考虑双边或多边的利益平衡,以尽力使各方利益达到平衡为核心出发点,使全球受益。 CCG副主任何伟文认为,为了更主动地发挥更大的作用,引领全球治理新规则的制定,要努力地、前瞻性地研究三个问题。第一,贸易是否影响就业的问题:自由贸易并未影响就业,阻碍就业的不是贸易而是科学技术。第二,自由贸易是否拉大了收入差距的问题: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在于国内政策而非全球化。第三,在努力参与并积极引领世界新的全球治理和贸易规则制定时,中国应当前瞻性地思考如何做到全面就业、充分就业和技术进步。龙永图希望中美两国智库针对各自在全球治理中的共同点和共同利益进行合作研究,给予各自的政府一些建议,以加强两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作用。文章刊于《国际商报》,2016年10月26日
2016年10月31日 -

【BWCHINESE中文网】中国五年后或将没有一流人才
今天的中国,就象一个身材不断增大,但血液却不断流失的人;有一天,等到身材完全长大(亦即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身体里的血却已流失殆尽。中国的精英正以惊人的速度离开中国,将来的三至五年后,跨国公司在华可能将找不到一流的经理人。 据中国和全球化智库(CCG)报告,2013年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达850万,且以中产为主,而移入中国的仅有84.8万。一些媒体将其称之为“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才流失。” 而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的报告显示,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居世界首位。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在节目中曾表示,按照今天中国教育的创新不足、社会的多元开放程度严重不足的情况,中国自身培养一流人才的进程将继续延缓,对外来一流人才的吸引力也将继续不足,同时一流人才的外流速度也在加速。 同时,他表示如果中国未来不做出深刻的改变。那么在将来的三至五年后,跨国公司在华可能将找不到一流的经理人。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王辉耀博士曾在2010年做过一份报告显示,对中国这么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我们的人才战略不仅是要吸收全球华人中的精英,而更要有胸怀和机制,吸引全球一流的人才;而恰恰在这方面,中国目前非常不成功,中国目前所谓的吸引人才重要还停留在吸引本国出去的“海归”,而远没到吸引全球一流精英的地步。 2004年开始实行的“中国绿卡”迄今只有四千多人获批,绝大多数获批者 是外籍华人,其中两千还是家属;而即便是在吸引“海归”方面,一方面这些年有一些“海归”回国,但高尖端的数量不多,而更多的知识移民则又对冲了吸引“海归”的功效。 李光耀表示:“中国是在十四亿人口中选人才,而美国则是全球七十亿人口中选人才。” 这使得中美两国的战略、视野、胸怀、机制、社会开放度立时活灵活现地勾画出来,高底立现。 有文章曾表示,未来世界20年中国在这些领需要一百万的顶尖人才。中国人口基数很大,人口数现在是美国的4倍多,那么而且我们现在就是说未来的这个发展如果要成为第一世界经济大国,我们必须要靠人才来做支撑。 中国从目前来讲,尖端人才是非常缺乏的,比如说可能按照科技部的统计,我们真正的高端人才可能在全国有一万人左右,就是特别顶尖的一批人才。 阿德麦肯锡曾经做过一个调研,以目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近35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么一个庞大经济体,中国大概需要75000个高端的一流的职业经理人,但是中国市场上只有5000个,差了十多倍。 据报道,美国则至少是中国的十倍以上,而且现在在很多尖端领域我们都很缺乏。中国现在是航空大国,拥有着仅次于美国第二大航空市场,而在航空领域的院士却没有几个;同样,作为全世界的第一大汽车大国,我们在尖端汽车领域的院士也非常少。 而在美国拥有着大多数的五百强企业,并且其人才储备是很充沛的,包括大学的人才储备;政府里面的人才储备,和科研研发机构的人才储备。另外,硅谷基本上是世界的一个创新中心。我们看到现在所有的这些高科技高发明这些新经济都来自于硅谷,但是硅谷里边50%的企业都是移民创造的,美国47%的科学家来自于不是出生在美国,包括他们的科技人才。 美国现在有200多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或者学者在美国工作,而中国这方面则基本长期没有。 但BWCHINESE中文网(ID:bwchinesewx)观察到的情况更糟的是,一方面,中国仅仅在十四亿人口中选人才;另一方面,十四亿人口的精英,又正在大规模、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等西方国家。 一是教育移民。 日本《外交学者》曾发表文章表示,中国学子对哈佛大学趋之若鹜,并非秘密。正如体坛精英加入顶尖俱乐部,中国的年轻才俊也被名牌大学所吸引。如今外国顶尖大学也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吸引中国尖子生。 无论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还是剑桥,一流学府都充满中国的年轻才俊。对个人这是好事,但其黑暗面就是国家的人才流失。 美国教育机构国际教育学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早在2010年来自中国大陆的赴美留学生人数就已经高达127628 人,与2009年相比激增了30%。并超过印度,成为美国接收海外留学生的最大来源地。 而目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各大院校在册学生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已经高达18.5%,也就是说,几乎每五名在校生中就有一名来自中国。 根据由华侨大学主编的《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 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9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包括国家公派、单位公派和自费留学)的总数为162.07万人,而学成归国人员总数仅为 49.74万人,约占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的31%。该报告还指出,目前仍在国外的留学人员有112.34万人,其中89.29万人正在国外进行本科、硕士、 博士阶段的学习或从事博士后研究、学术访问等,并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 而在2013年出国留学人数已经达到40万人,我们总数出国人数的大概260万人,但是,回来工作的人不到一百万,超过60%会移民到海外,这个是个相当大的比例,一般国际上常见的大概40%、50%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比例。并且60%多的人中,高端人才在海外的比例非常大,比如博士毕业生,理工科的博士90%留在了海外。 按照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最新的统计,返回的27万人中,9万人做了留学认证登记,但其大部分是硕士生,其中很多还包括在英国一年的硕士,而博士只有5%。 其二是投资移民。 中国有不少富豪精英移民海外,而且每年的增速很快。据调查,在财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富豪中,想要移民到美国的人占40%,想到加拿大的占37%、想到新加坡的占14%、 想到欧洲的占11%。有专家认为,中国精英移民海外或将造成中国的人才流失。 投资移民不仅意味着我国的人才流失,还意味着我国的财富流失。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9年起,每年随中国内地富豪流向海外的财富达到 100亿元以上,有八成以上的财富贡献给了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还有不到两成被欧洲各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瓜分”,受益者还包括塞浦路斯、韩国 等非传统的移民目的国。 美国移民局数据显示,中国富人通过投资移民流入美国的资金每年最少达到29亿元。据英国内政部数据,2010~2011财年,中国富豪一年向英国至少“送去”了5亿元。来自澳大利亚移民局的数据显示,中国投资移民一年“贡献”给澳大利亚的财富最少也达到32亿元。 中国通过投资移民海外的基本上以社会高中收入人群为主,他们同时也是社会各个领域中的精英。投资移民不仅带走了庞大的社会财富,更是人才资源的巨大流失。 人才资源的大量流失增加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后继乏力的风险,科技精英、文化精英、金融精英的流失不仅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轨,也限制了文化实力与竞争力的提升。 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是因为调动了国内低端劳动力的流动,减少它的壁垒,把劳动力全球化。两亿农民工的流动带来了繁荣,而未来30年却要走到瓶颈。 中国经济已经放缓,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3%,增幅创下近6年新低。而且人口红利正在下降。而现在则是人口红利加上人才红利,两个红利同时在下降。 有评论曾表示,中国面临一个新的转型,就是我们要从人口红利转到人才红利,要从中国制造转到中国创造,要从投资拉动转到人才拉动,那么这些方面的话都要靠人才来支撑。中国过去的主要财富是依靠靠出口,而中国出口的商品又不具备高技术含量。 在过去这些年,中国企业占世界500强比例在不断的增加,从原来的几家,后来十几家,二十几家到去年大概六、七十家,但是进入500强企业,却没有多少真正是能在世界上就占领国际市场份额,能够占领国际市场的。从这方面讲,真正意义上全球化的公司,屈指可数,联想、华为以及前段时间在美国上市的阿里巴巴。 之所以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缺乏大量的一流的国际化人才,比如顶尖的这种世界五百强的这种高管。 BWCHINESE中文网财经观察员认为,未来30年需要靠全球化的人才流动,我们需要发挥全球人才的红利,吸引全球人才来中国。特别是要把移民出去的人才吸引回来,再加上国际上的其他国家的人才能吸引到中国来,才能给中国一个支撑未来30年的发展。 中国领导人也强烈意识到这种人才赤字,尤其是位于学术金字塔上层的高层人才,中国正在发动一场人才争夺战。为吸引精英人才回国,北京实施“千人计划”,但收效有限。尽管企业家们正回到生机勃勃的新兴风投文化中,但中国并未成功地吸引其他人才回国。(作者:国际观察员 角卜升)文章选自BWCHINESE中文网,2016年10月27日
2016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