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国际组织、区域合作和“一带一路”是CCG全球化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最早以全球化命名的智库,CCG创办了“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并设置全球化相关国际议题;在海内外举办了“WTO改革”、“多边治理”、“一带一路”等专题研讨会,把“一带一路”这一主题首次带到国际安全与治理领域的世界高规格会议——慕尼黑安全会议。基于多年对全球化领域的全面研究,CCG发布出版了《“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共赢方案及实现路径》,《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全球化向何处去:大变局与中国策》等研究报告和图书,其中Edward Elgar 出版社出版的Handbook on China and Globalization是为数不多的由智库在国际权威学术出版社出版的全英文书籍。CCG提出的两项倡议入选首届巴黎和平论坛,为中国智库更充分参与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开拓了崭新模式。此外,CCG与WTO、UN 、经济合作国家组织(OECD)、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众多国际组织、国际智库和相关机构建立了良好的长效合作机制。
-

赵慧君:创新构建科技人才交流合作的治理体系
2019年7月13日,由全球化智库(CCG)和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全球人才流动和国际移民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科技部引进国外智力管理司副巡视员赵慧君在开幕式致辞。她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科技全球化的推动者和受益者。目前,中国已与全球160多个国家建立了科技交流合作。科技交流合作最重要的是人员交流,而全球化新阶段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需要人才。中国应继续推动科技创新领域扩大开放,促进人才交流活动,共建更加有利于国际科技人才流动的环境。 以下为赵慧君女士在“第三届全球人才流动和国际移民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全文精编: 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由全球化智库和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全球人才流动和国际移民学术研讨会”。 开放创新是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基本特征。中国一直都是科技全球化的参与者、受益者,也是推动更广泛创新合作的贡献者和引领者。近年来,中国全方位地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努力构建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创新共同体。目前,中国已经和160多个国家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签署了政府间合作协议110多项,人才交流协议340多项,参加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超过200个。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起点,科技交流合作最重要的是人员的交流和互鉴。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科技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和合作更加频繁和密切,也使参与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获益匪浅。 今天的中国,我们感觉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这些年里,我们通过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构建有利于吸引人才的政策环境,通过实施更加务实的人才引进政策,对外国人才来华签证、居留进一步放宽条件,简化程序,依法保障外国人才在中国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去年,我们累计发放外国人才工作许可33万份,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已经超过95万。 面向未来,中国将进一步扩大科技对外开放合作,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务实的举措和良好的环境,欢迎全球各地的合作伙伴和优秀人才来中国创新创业。我们作为制定和实施促进科技人才开放实施的政府管理和服务部门,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在科技创新领域扩大开放,深化人才的交流合作。我们也十分期待在今天的研讨会上,听到各位专家的真知灼见,给我们更多的启示,让我们共同为构建更加有利于科技人才交流合作的治理体系做出努力。 祝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第三届全球人才流动和国际移民学术研讨会”由全球化智库(CCG)和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是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后国内举办的国际性的关于人才流动和移民研究的高规格学术研讨会。本届大会以“世界的中国:迁徙与交往70年”为主题,就中国的人才流动现状、出入境政策、移民管理与服务机制、国际移民治理理论与实践等重大议题进行学术探讨和政策建议。人社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科技部、北京市人才工作局、国际移民组织、经济合作组织、国际大都会项目委员会以及高校、研究机构等国内各部委、国际组织和产学研各界专业人士近三百人共同参会。 2019年正值建国70周年,历经70年发展征程与四十余年改革开放,中国形成了“人才磁场”也见证了全球人才环流的加速。去年,CCG十年推动的国家移民管理局正式成立,是中国移民管理体系和人才制度的重大突破。本届研讨会的举办旨在于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紧扣改革开放成就,不仅聚焦如何通过迁徙与交往加深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也更好促进中国对世界的融入,以期为世界与中国的学界、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的研究带来思考,启迪共同努力的方向。CCG也将继续充分发挥国际化社会智库的优势,设置前瞻性议题,邀请海内外移民专家共聚思想智慧,为进一步促进全球化发展和全球化治理相关研究积极建言。 (本文根据赵慧君女士在全球化智库(CCG)于2019年7月13日举办的“第三届全球人才流动和国际移民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9年7月31日 -

何宪:扩大中国对国际人才吸引力的同时,也需应对出现的机遇和挑战
2019年7月13日,由全球化智库(CCG)和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全球人才流动和国际移民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国人才研究会会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何宪在开幕式致辞。他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全球人才流动成为当今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特征和一大趋势。现在的中国正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的新格局。如何在扩大中国对国际人才吸引力的同时应对出现的机遇和挑战,是当下亟待研究的问题之一。
2019年7月31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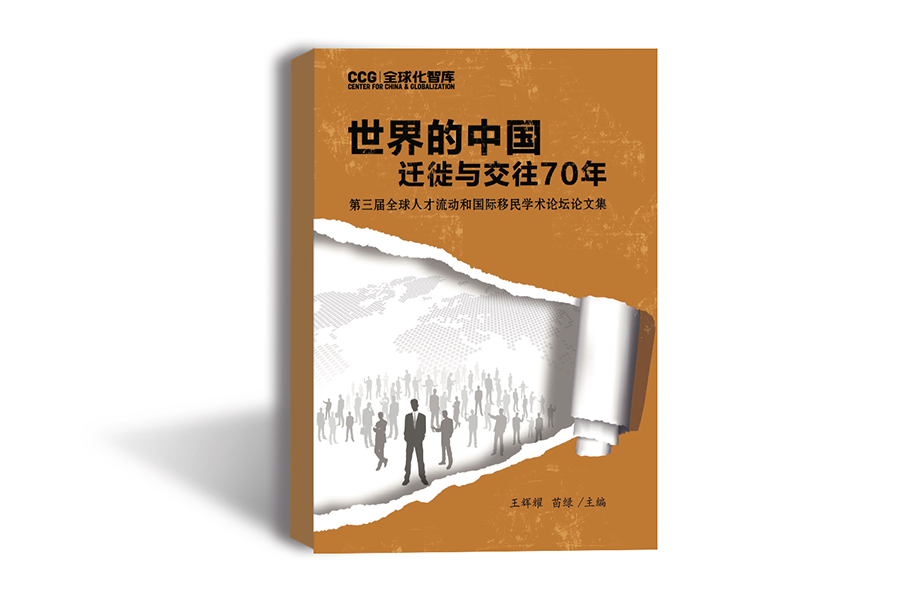
世界的中国 迁徙与交往70年——第三届全球人才流动和国际移民学术论坛论文集
目 录 第一章 新型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的华人华侨 国籍确认存在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华人移民与人类的全球化进程…………………………… 07 难民危机冲击下欧洲华人面临的挑战………………………………………………………… 34 沟通中国与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历史功用与现实启示……………………………………… 48 浅谈法国华人流散群体的商业发展与地理分布——以大巴黎地区为例…………………… 68 第二章 人才竞争的多层次、合作和比较方法 流动生活实践中的世界主义——以瑞丽罗兴伽人珠宝商的认同研究为例………………… 81 外籍劳工政策对工业化进程的影响——以工业化起飞阶段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为例(1970-1990)……99 移民政治:全球化时代的美国现代国家建构和人力、人才竞争中的政治文化双向驱动悖论………122 科学家流动对科研合作的影响 ……………………………………………………………………142
2019年7月5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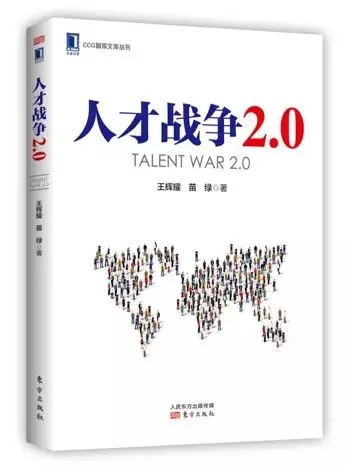
CCG研究 | 德意志:“回到德国!”到“欢迎来德国!”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 全球对技术人才的争夺将越来越激烈,因此德国必须修改移民法规,使得德国对海外人才更具吸引力。 ——德国联邦内政部(Bundesministerium des Innern, BMI) “回到德国”!2001年8月27日,写着这样一句标语的横幅被飞机拉开,在纽约和加州海岸两地上空不停地盘旋展示。美国是流失在海外的德国人才的主要集中地。二战时期,纳粹主义兴起使许多人才流失,在德国失去的13名“未来诺贝尔物理学家”中,11名就去了美国;二战后也有3名物理学家去了美国。 这仅仅是人才流失的冰山一角。对此,德国政府发出了强力的召唤——“回到德国!”从德国的国际电台“德国之声”开始大力宣传,再到美国媒体上打广告,最后还在新兴的互联网进行宣传。两年后,“德国学者协会”在美国正式成立,为优秀的德国人才回国牵线搭桥。 吸引人才回流只是德国参与人才战争的一个侧面。 早在二战结束后的20世纪50年代,德国便开始放松移民政策 。当时因经济腾飞,德国面临人才与劳动力短缺问题,启动了著名的“客籍工人计划”,1960~1966年共招募360万外籍工人到西德工作。从2000年始,德国从长期制度建设上应对人才战争。德国IT业出现人才紧缺,时任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推动实施“绿卡工程”,对外国人才实行优惠移民政策,要求是信息、通讯等行业高级技术人才,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凭,已达成年薪不低于10万马克的工作协议,最长期限为5年。2005年1月1日,德国《移民法》正式生效,这在德国历史上是首次,表明德国承认自身是一个移民国家,此后调整移民政策专门为人才战争服务,为刺激经济、引进外资开放了投资移民政策,在移民立法中增加了面向高技术人才的积分制度,外国人才可以凭借投资和技能成为永久居民和入籍。 德国的选择,是对劳动力短缺现实的回应。2004~2015年十多年来,德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人口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处于萎缩状态。2012年开始,德国的移民人数激增,至2014年在德生活的外国移民数量达到1090万,创下历史纪录,相当于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有移民背景,然而2015年德国国内仍有568743个岗位空缺找不到人来填补。 德国的经济发展既需要低技能劳动力,也需要高技能劳动力来满足IT等行业的需求。2013年4月,德国政府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推出“工业4.0”战略目标,随之成为国家标签。想象一下,你要买一辆汽车,只要拿出手机,点击应用软件,输入你的定制要求,然后坐等工厂生产、组装和配送就行了。这就是“工业4.0”时代,它的到来亟需高水平人才,尤其是在计算机、电子工程、电气化、机械工程、人工智能等领域。Make it in Germany 是德国联邦劳工及社会事务部(BMAS) 和德国联邦经济事务与能源部(BMWi) 建立和管理移民工人务工的网站,特别强调德国非常需要数学、科学、信息技术和科技领域(德语缩写MINT)的精英移民人才。 事实上,德国“工业4.0”的兴起和实现都离不开外来移民中的高精尖人才。德国首位机器人专业的汉堡科学院院士就是华人张建伟,他1989年获得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人工智能专业硕士,2004年获得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计算机系机器人专业博士。随后,他在德国从事及领导“工业4.0”中的感知学习和规划、多传感信息处理与融合、智能机器人技术、多模式人机交互的研究与开发,发表三百余篇论文及专著,并多次获得国际会议最佳论文奖,指导德国硕士百余名、德国博士三十余名、洪堡学者多人,本人还拥有四十余项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方面的发明专利,任数个国际重要机器人及人工智能会议的主席、多份国际专业杂志编辑,并担任德国数家企业的技术顾问,可谓国际顶级机器人专家。 作为欧盟创始成员国之一,德国的移民政策深受欧盟相关政策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影响,尤其是欧盟2009年出台的蓝卡计划(Blue Card) 。蓝卡出台的背景是欧盟的高素质劳动力中非欧盟人口占比例太低,仅0.9%;相比之下,澳大利亚为9.9%,加拿大为7.3%,美国为3.5%。2007年,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认为,欧盟成员国需要对非欧盟高技能人才的录用及长期居留做出统一规定。2009年蓝卡正式出台,允许非欧盟高技术移民申请在全欧洲境内的工作许可。 德国2012年才全面实施欧盟“蓝卡计划”,此后迅速成为欧盟蓝卡的最大发行国,2013年发放的“蓝卡”有90%来自德国,彰显出德国在全球范围内争夺高水平专业人才的攻势。欧盟委员会对此颇有微词,认为一个国家“蓝卡”签署数量太多,正显示出该计划的失败,因为没能够在欧洲平均分布这些高素质的非欧盟移民人才。德国联邦统计局2016年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德国移民数量及净增移民数量均为史上最高。 与美国、加拿大相比,德国对留学人才的运用相对欠佳。德国的公立大学教育实力很强,而且不收学费,接收的外国留学生主要来自中国、印度以及东欧地区,整体上因科研支持不足、就业市场压力大、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较高等原因,较难挽留优秀的外国留学生。不过这并不绝对,一些博士毕业的精英还是被德国成功挽留,如上述张建伟博士。还有一些优秀留学生被德国机构或企业聘用,如上海市知联会外企分会副会长刘斌博士,他获得德国乌尔姆大学胰腺外科专业博士学位,决定“弃医从商”,进入德国具有160余年历史的“隐形冠军”老牌医疗设备公司爱尔博(ERBE),在总部工作和培训一年以后,2000年回到上海开设代表处,至2015年业务量增长33倍,销售业绩从全球32位跃升为前3名,受到德国总部的专门表彰。 2015年以后,德国专业人才会出现青黄不接,并将严重影响德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德国出生率低,德国人口正快速萎缩,而德国机器需要更多工人!当年德国宣布接收80万难民,是2014年接收人数的4倍!这背后的考量之一是德国技术人才供求不平衡,难民潮恰可为德国提供许多高素质人才,如工程师、学者、专业技术人员等;而且德国不仅需要工程师,还需要普通劳动力,如医疗护理人员,人手更短缺,非常适合难民。 然而,随着成千上万的难民从战乱的中东地区涌入德国,恐怖分子也混杂其中,德国有些“消化不良”,涉难民的非法和暴力事件频发,新闻爆出在德中国女留学生也遭受难民的侵害。“大救星”默尔克陷入悲悯与两难的境地,总理之位遭受来自全德的挑战。面对既成事实,无论默克尔政府或新一届德国政府,接下来的挑战是如何安置难民,让其中的人才有用武之地,把年轻的劳动力培训成德国需要的人才,以及克服难民潮带给德国乃至欧洲社会的冲击。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人才战争 2.0》, 王辉耀、苗绿著,东方出版社。
2019年2月26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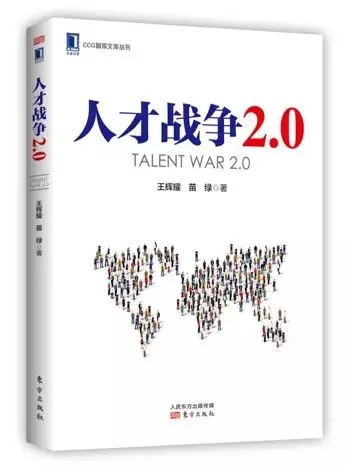
CCG研究 | 澳大利亚:青睐职业人才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 跟矿业的繁荣不同,创新思维的繁荣(ideaboom)是可永续发展的,唯一的束缚就是我们的想象力。 ——澳大利亚现任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 2016年4月,逯高清出任英国萨里大学第五任校长,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留学生中首位出任英国排名前十大学校长的人。此前,他在澳大利亚求学、工作了28年,从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攻读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到成为全球备受尊重的学术带头人,从39岁成为澳大利亚工程院史上最年轻的院士到2014年升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史上第一位华人副校长,他为澳大利亚的纳米科技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其他被澳大利亚吸引的华人精英有:杨小凯,澳籍杰出华人经济学家,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黄英贤,现任澳大利亚吉拉德政府金融部长,也是首位亚裔部长和华裔部长;苏震西,祖籍中国广东顺德,17岁和家人从香港移民至澳大利亚,后来成为墨尔本第一位直选市长,也是该市首位华裔市长,并荣获“世界最佳市长”荣誉……他们有的从事学术研究,有的从政,均为澳大利亚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一直以来,澳大利亚是人才战争的大赢家。在这个奉行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度里,2015年接受的移民存量为676.4万,占本国人口的28.2%,比加拿大高出6个百分点。其中英国人最多,约129万人;新西兰人居次,约64万人;中国人居第三,约45万人,相当于每吸收15个移民中就有1个是中国人。 2015年9月走马上任的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的儿媳妇也是华人,他还曾到中国开设了第一家中西合作的矿山企业河北华澳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从5万多年前第一批移民通过马来群岛和新几内亚抵达澳大利亚,到成为英国流放犯人的落脚地,到1788年对外开放移民,直到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始终有着“人口少得可怜”的烦恼。从1907年起,澳大利亚开始大规模接受移民,但限制有色人种,奉行“白澳政策” ;二战后,大力吸引欧洲人移民——“只要你是欧洲人血统,身体健康,没有犯罪记录,就能够成为澳大利亚的移民”;1950年,允许亚洲学生赴澳留学;1957年,非白人移民在澳洲居住15年后可以成为公民;1965年,“非歧视性”技术移民计划开始实行,任何种族的人只有达到职业技术要求,都可以申请移民;1966年,部分非欧洲移民在居留5年后可获得永久居留权和成为公民。 1973年是澳大利亚从“人口争夺”过渡到“人才争夺”的转折点。得益于工党政府的努力,“白澳政策”被正式取消,自愿移民数量超出国家所需数量,澳大利亚再也不需要发放津贴来吸引外来移民了!到了80年代,鼓励“多元文化”和“多种族和谐”被正式确立为国策。 澳大利亚的两个主要政党,工党和自由党,竞选时势均力敌,各不相让,但在移民政策上惊人得一致:均支持高数量!2015~2016年度,澳大利亚吸引了近19万名移民,其中近13万名通过“技术渠道” ,近6万名是家庭团聚类,308人获得特别资格类别永居签证。 其中技术类、投资类、雇主担保类人才占获永久拘留资格总人数的68%,这一比例多年来保持稳定,相当于10个人中有7个是职业型人才。 怎么争夺海外的职业型人才?澳大利亚采取的办法如下。 20世纪90年代开始施行以需求为导向的移民政策,确立职业型移民制度,采用职业移民清单方式,并借鉴加拿大的积分评估制度,结合起来瞄准海外的技术人才和商业人才。1999年澳大利亚政府开始使用“紧缺职业列表”(Migration Occupations in Demand List),符合表单上的职业才能申请移民。2011年,又引入“技术选择”(Select Skill)移民模式,海外申请人需向移民部递交申请书,政府选择匹配合格后向人才发出邀请,这就相当于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全球人才储备库”,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地调取人才。 为了吸引投资者,2012年澳大利亚政府在商业创新与投资项目中新增“重要投资者签证”,2015年7月1日又实施“高端投资者签证”,要求申请者投资超过1500万澳元,投资满一年即可申请永居权。 为了吸引留学生,澳大利亚自2007年9月1日起给予18个月毕业后的临时签证,还对境外著名大学(亚洲18所,中国占12所 )毕业、符合澳大利亚紧缺技术需求的学生给予18个月的临时签证,不受限制在澳境内工作、学习或者旅游。双管齐下,既使澳大利亚的国际留学生比例远超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值,还从中国等国家“掐尖”,把国外顶级大学培养出的人才招揽走。 为了吸引优秀的科技人才,2009年澳大利亚发布了《驱动创意:21世纪的创新议程》,缔造科研环境基础;2010年降低了赴澳读研究类硕士、博士的门槛; 2016年11月生效“创业者签证(Entrepreneur Visa)”,吸引有创新及高增长潜力想法的创业者留澳,并协助在澳接受高等教育的高级人才、博士或研究类硕士留学生,尤其是STEM 和IT领域毕业生留下促进国家改革创新。 为了促进偏远地区的发展,澳大利亚设立了偏远地区雇主提名计划(RSM),雇主可以提名来自海外的员工或者境内临时居住者来填补全职的、永久的空缺职位。 澳大利亚瞄准的是全球的职业人才,2009年移民局在曼谷、北京、洛杉矶和马尼拉4个城市举办技术移民招募会。 尽管使劲浑身解数,澳大利亚研究部门还是认为政府引进人才的力度还不够,要更加重视人才战争,要从全球人才市场吸收到足够的稀缺资源——世界顶尖人才。早在10年前,澳大利亚便认识到“即使在过去10年内澳大利亚的技术和工程人才队伍有所增长,但世界级人才仍短缺”。因此,澳大利亚善用中介机构与猎头,把政府公务员、大学校长、高级精英人才等的聘请委托给专业猎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公开竞聘。 事实上,国际移民组织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吸引到的移民质量还是很高的,移民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更高达46.4%,远高于美国的27.3%和加拿大的33.2%,有效补充了本国所需的稀缺人才。 2015年澳大利亚人口增速为1.4%,为10年来的最低值,工作年龄人口近年增长也很缓慢,老龄化问题严重。特恩布尔曾表示将扩大政府的技术移民计划,以吸引并接纳海外优秀人才。还有研究认为,澳政府可能会大力推进商业类移民政策,以吸引更多海外投资。2016年初,澳大利亚产业组织(Australian Industry Group)向澳政府提议将每年引进的海外移民数提高15%,从19万人增加到22万人,以助推本国经济发展。 正如前移民部长克里?伊文斯(Chris Evans)所说,澳大利亚被认为是全世界通过移民政策吸引人才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没有任何理由不继续坚持。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人才战争 2.0》, 王辉耀、苗绿著,东方出版社。
2019年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