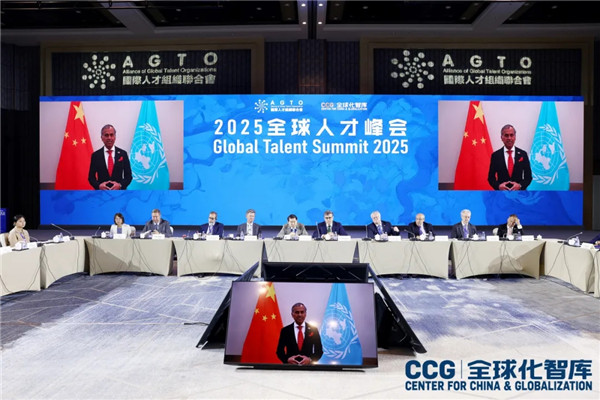储殷:拿什么来切实提高乡村教师待遇
2017年11月30日近日,一则有关北京市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的新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文 | 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储殷
近日,一则有关北京市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的新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据报道,北京市根据所有乡村和山区镇区中小学校距离北京城市中心的直线距离,将乡村和山区镇区学校划分为五大类,本着“越往基层、越是边远、越是艰苦,地位待遇越高”的原则,每个月的补助从1400元到4000元不等。
从2016年9月至2017年10月,全市共为乡村教师发放了超过9亿元岗位生活补助,显著提升了乡村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一时间,乡村教师待遇问题再次引起社会热议。尤其引起大家讨论的是,北京作为首都,经济发展水平高,欠发达省份和地区,其财力是否可以支撑呢?
其实,自从2015年国务院出台《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以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先后出台了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的政策。根据今年9月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实施评估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共投入补助资金44.3亿元,比2015年增加了9.9亿元,提高了28.8%。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实施县中,人均月补助标准达到或超过400元的县占25%,与2015年相比提高11%。应该说,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得到了全面落实,政策覆盖面不断扩大、补助标准逐年提高,乡村教师支持计划落实卓有成效。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目前各地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进度不一,从面上来看,仅仅是落实了“生活补助政策”,而且覆盖面不够广,标准依然偏低,许多贫困地区乡村教师仍然享受不到这一政策。
而在“生活补助”之上的更高层次的激励,则只有北京、杭州、上海等少数发达城市才能实现。此外还有乡村学校教师编制严重紧缺、特岗教师制度落实缓慢等系列问题。总的来说,乡村教师问题是一个系统性问题,而其中的关卡是待遇问题,待遇问题主要是发展不均衡不充分。
首先是发展不充分的问题。这是由我国义务教育经费县级财政为主的投入机制决定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地方财政不堪重负,又拿什么来切实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呢?根据国家审计署2011年公布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高达10万亿元以上。根据财政部预算司公布的数据,2016年,我国地方性政府债务限额超过17万亿元。
事实上,从发达国家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的经验看,义务教育经费要么由中央财政保障,要么由省(州)财政保障,而绝不可能靠县级财政。一方面,县级财政很可能无力承担;另一方面,县域均衡也是不合理的,因为人才并不会永远留在本县;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政府会节省办学资金,势必减少对生源较少的乡村学校的投入,最终与国家要求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目标背道而驰。
其次是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从实践来看,当前我国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和分担机制放大了各地的经济实力差距,能力强的多补,能力弱的少补,比如杭州早在中央出台《乡村教师计划》之前就已经提前实施了部分利好政策,而中西部省份的许多县市至今也拿不出钱来增加投入;多补的就能更吸引到更好更多的人才,少补的则更难招引和留住教师;越是欠发达的地区,却越需要加强乡村教育,这就形成了“马太效应”,成为恶性循环。
此外,根据现行的扶贫机制,对于大部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国贫县,国家转移支付使其基本可以承担政策落实所需的财政支出。而对于部分省贫县及部分经济欠发达但非国贫或省贫县,自身财政能力难以承担政策实施所需的全部配套经费,从而造成“两头好、中间塌”的怪相: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自己解决经费,最贫困的地方国家解决经费,而不上不下的地方则没法解决经费。
因此,笔者认为,一方面,乡村教师待遇提高绝不能仅靠县级财政,必须加快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建立中央、省、县三级保障机制,尤其要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的投入,从而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另一方面,应该建由中央统筹,建立分级差序格局的财政分担机制,补齐不同类别地区的财政缺口,保证各地乡村教师待遇提高的政策能够协同实施,从而解决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文章选自法治周末,2017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