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位置:
- 首页>
- 活动>
- ������������
������������
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
毛大庆:谁是新的世界公民?
理事简介毛大庆,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UR WORK 创始人、董事长。去年上海追踪科技生活节,到今年参加北京的科技生活节。的确,科技只有真正落到生活里,才是有意思、有用处的科技。以下为7月28日在 "钛媒体 2018T-EDGE 科技生活节" 上的演讲内容,主题为《混合内容再造城市空间》。 刚才听贺晓曦(笑果文化联合创始人)的分享,里面多次出现了两个词:场景,内容。 科技对社会的推动,以及生活的变化,尤其这个时代人类的科技和技术进步,我们面对着难以想像又无比期待的未来可能出现的革新,我想这些不断推陈出新的科技产品一定会再次颠覆我们对现在习惯场景以及生活种种内容的认知。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这样的递进过程,我们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到今天以信息和数字化技术所推动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共享经济。城市是一个最应该被科技所改造的对象,城市也是最应该被科技所颠覆的最大素材。在城市里,我们赖以生存的一个巨大物理载体,我们未来会看到林林总总的各种不同,晓曦其实就是在城市变革里生产内容,这是我们平台上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素材,我相信这样有爆发力的素材以后会越来越丰富。我想,科技改变的是我们对生活场景和社会场景的各种认知。那么,在共享经济的背景下,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颠覆,并释放了巨大的能量后,生产力成本降低,人们在各自的能力和能量场下,可以做自己的发明、创造,以及各种各样的抒发。这都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特征。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物质超级丰富,人类不再被物质绑架的时代,所以,下一个时代,城市向一种更开放的共生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极高。新公民的推动力我们每天都在想象,我们的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中国有 160 亿万方的城市存量空间,未来,在科技推动下,科技和生活充分结合,会有非常大的想像空间和创作场地。未来的城市空间会逐渐演化成一个高智空间,也就是高智力和高效能。空间里一定要有内容来填充,笑果文化就是一个新消费探索中成功的内容运营商。年轻人会把内容当做找到同样标签伙伴的场景和参照物,用相同的内容,去圈定相同的群体,同时他们愿意为找到同好而付出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成本。智慧化空间、社群化引擎,最终一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超级平台。钛媒体未来将成为一个超级平台,优客工场同样也是一个超级平台。我们最多所做的事情是充当社群化的引擎,以及各种智慧化的分享,这也是未来城市创作、城市被科技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但不论什么,这些东西都是物理的,最终在里面最活跃的还是所有的人,人才是根本。下一个 20 年里,四类人群将推动着平台的扩展,同时也最大化的利用着平台的能量:新青年、新工匠、新农人、新老人。 新青年、新工匠、新农人、新老人首先与大家分享几个数字,我们说的新青年更多讲的是 1985-1996 年出生的 1.84 亿人,这 1.84 亿人口就是我们无论做什么新内容,无论做什么新技术,最重要的、现在针对的对象,这一批人也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自由实现梦想和自主意识下,能够实现各自的创造价值的第一代人。第二次人口高峰之后,再也没有这样的高峰了。1985-1996 年会是今天中国改造社会形态、改造社会消费形态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另外一个群体是 1966-1974 年出生的 2.94 亿人,这一群体会变成非常有消费力,非常有格调,非常讲究品质的一代新老人,这两拨群体大概有 5 亿人,这 5 亿人会构成未来 20到30 年间,中国重大的各种消费形态和社会形态创新的两拨非常重要的推动力。新工匠也会在这 1.84 亿人中诞生,这一群体会更加重视品质,会更加重视生活和工作的结合,工作和生活的无边界化,我想是未来创新和创造主要动力来源。最后,在 2.2 亿人的新农业人口里,这一群体不再会安于做简单的农民工,他们也不会简单地在城市做低端的劳动工种,而会慢慢变成更高级的职业化工人,他们不再是父母那一辈扛大包的人,所以新农人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社会新消费群体。新青年、新工匠、新农人、新老人会是未来构成科技和生活结合推动力的 4 个主要推动手。这四个群体中将涌现更多新的创造力阶层代表,多元化的消费社会必将取代购买力社会,购买力社会将逐渐进入到多元化的消费社会,多元化消费社会中的新阶层,来自于各行各业,不分性别、年龄,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展现出持续的创造力和活力。这些人会是社会创新的参与者,新消费精神的推动者,以及新生活方式的引领者,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而且我们在做任何一种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时,所瞄准的对象可能都逃不出这四个群体。新的群体标签和特征:工作、生活、兴趣和社交我们谈了城市、推动者、享受者、影响者,我们也谈了新的社会阶层,我们看看新的社会阶层有四大特征: 特征一:工作在高度融合工作和生活方面,会使得产生一大批具有工匠精神的人,他们更重视工作和兴趣的高度统一。在生活上,这一用户群体和这一新消费者群体更关注内心的体验。今天做任何产品,包括我们做城市空间产品,特别重视的颜值和内容,住用户的眼里,这两点才能真正打动他们的内心。特征二:生活关注自我内心体验:一是颜值,二是创意。成功的产品,首先要有辨识度,然后才能讲消费体验。必须抓住用户的眼睛,再谈抓住用户的心。特征三:兴趣跨越边界的兴趣产品越来越多,人们不再局限在自己一个专业内,和一个单一技能内,他们更愿意去探索那些他们不熟知的领域,去寻找找到他们更多的兴趣点。特征四:社交跨文化的体验,这一代人和下面几代人,85-96 年、96-00 年,这一批人他们思想和思维更多元、更包容,他们的心态更折中,边界这个词将会逐渐淡化,直至消亡。新的世界公民就会在这些人里面诞生,这些都是我们说当科技和生活结合之后会诞生的新兴人类。线上线下产品 并不局限在交互性在线下交互的便捷性,是智慧城市和智慧场景创造出的非常重要的价值。 优客工场创立 3 年多,目前服务了 22 万人次,一万多家企业,这里面有四五十个独角兽级别的企业,有十几家 A 股上市公司,以及 49家新三板企业。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看见了这些企业跨越了 47 个大行业,100 多种带有各种创新趋势的子行业,这些人在一个共享空间、共享平台上,形成了各种自组织、自链接、自服务、自管理,这是我们特别乐于看到的。当线上的生活饱和之后,人们更多的希望在线下寻找多元化的场景,而多元化的场景又会折射到线上,并推动线上的各种模式发生改变,从社群和社群的连接,慢慢会形成价值观的叠加,这是我们在城市空间的多元化和城市空间内容再创造里面发现非常有意思的新方式和方向。在优客工场线下企业越来越多以后,我们逐渐形成了线上庞大的社区,在线上大概聚集了 1 万多家公司,现在我们慢慢的把很多和它们相关联的外围公司,都吸纳到我们的平台上,在平台上形成企业的多维度、多元的评估系统。企业的集结、企业服务、企业社交、企业服务的应用,在平台上逐渐自我形成的社群,这是在线下空间里共享之后,我们发现的非常有意思的一点,这一点也让我们坚定从空间到服务,慢慢走向更多元的服务叠加非常重要的思维方式。你走进的不是一个空间,而是一台机器我们也在城市空间的更新、升级、改造时,研究了各种各样在科技场景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我们列举了这 15 个科技场景,以及能够提供的科技服务,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在平台上进行重新整理,在一个平台上进行多元化的运营。最近我们和联想的 ThinkPlus(智能生态战略) 正在研究这 15 个场景的集成度,很快在北京翠微路一个新的优客工场社区中,将呈现出它们集成后的办公模式,这个非常好玩,当你进入这个空间后,就好像进入了一台机器,而不是一个房子.我们更希望城市空间未来逐渐都能成为智慧城市的细胞,甚至是一个小枢纽,让社群形成更快速的连接。 优客工场为未来的办公空间搭建了一个 IOT 和智能化办公的场景模型,我们想像中未来每一个楼宇、空间、办公场景,都应该是由无数个智慧细胞组成的,楼和楼可以说话,空间和空间可以传递信息,各个空间之间的人,可以去发现你们相互的朋友和需要找到的对象。 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每一个空间都应该是一个智慧枢纽,以及智慧港口,这是我们对未来智慧空间场景的想像。在线上,优客工场的APP优鲜集,经过了一年多的迭代后,沉淀了近 34万条各种各样的个人数据,以及11000多家企业在平台上使用的各种点的数据,我们希望通过线下平台的企业聚集,以及线上平台把各个不同的办公空间的人聚集在一起,让他们的各种服务交互在平台上沉淀各种用户使用习惯数据,从而能更好的推送,以及形成他们的画像。在这一点上,数据挖掘慢慢形成很大的价值,最近我们也在开发两个新的东西:第一,当客户到访,来咨询空间使用时,当客户到访的一刹那,用户的画像能够自动在接触你的第一人时就形成了。这一点在房地产行业内做的最好的是链家,链家就是从用户到访的数据抓取开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城市用户数据,以及今天城市楼宇点。第二,我们也希望通过优客工场社区内带有芯片的智能桌子去扑捉用户的动态轨迹。这也是我们最近在开发的内容。将来每一个桌子的使用者,实际上就是智慧节点用户,同时还是智慧节点的参与者和供应者。 今天,全球有有 72000 人使用优客工场的桌子,当这个数字变成 10 万张、20 万张桌子甚至更多时,大家想象一下,每一张桌子前的用户都是一个智慧港,头脑和头脑之间的交互将会通过无数张办公桌实现,空间的连接将变得超级便捷和快速。多元化空间生活场景的商业实践同时,过去的两年多里,我们打造了另外一个产品:共享际。我们的目标是能够更精准的连接 C 端用户,我们把居住和共享办公、更好玩的餐饮、娱乐、剧社,以及刚才谈到的喜剧、体育群体,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创造了一个多元化生活场景空间,就是把住、社交公寓、共享办公、更多的消费 IP,联系在一个城市空间里,这是我们在过去几年里,各种各样的生活场景,包括有社群交互、喜剧交互、文化交互,体育社群,以及各种各样城市创造力的居住人群。我们始终不把它叫做青年公寓,而称之为社交型公寓,我们希望居住者能在这里找到朋友、圈子、组织,同时他们可以愉快地形成自组织。我们现在有一个特别大的群,就叫共享客,共享客都是在我们这儿居住后留下了痕迹,还交到朋友的人,他们在这里有共享厨房、共享剧社、共享健身,有各种各样社群组织。例如笑果文化这些有趣的平台,同样都是我们平台上的合作方和合作组织,它们进来以后,能够跟共享际的餐饮组织、体育组织发生更多的混合和叠加,产生巨大的爆发能量和价值能量。当然,我们也会通过 APP,包括线上各种各样的活动寻找更多的组织,让更多的组织和群体在我们的平台上落地,让组织和组织之间再产生组织黏性。原来我们总说一个 C 端黏性,形成一个组织,现在我们希望做到组织和组织之间的流量互换和 IP 的叠加。对城市而言,核心的商业方法,就是在科技与生活结合以后产生的混合内容。多样性×文化智力=创新?在前年我翻译了一本书,叫做《为谁留的空椅子》,这个里面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概念,就叫做多样性 × 文化智力 = 创新。这一点我在几次走访硅谷之后,特别有感触,这个时代最难以逆转和难以控制的就是多样性,当我们把多样性和有文化智力的人叠加以后,真正的创新才能产生。创新最好的地方和最能产生创新的城市,就是多样性非常丰富,同时文化智力发达的人聚集的地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共享办公、共享居住场景下的这些空间,都能成为文化智力高度发达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2013 年,我在哈佛大学和王石有一个对话,当时我问王石,什么样的城市估值最高,他说估值最高的城市可能是波士顿,可能是旧金山。这些地方的单位密度、单独城市空间里的聪明头脑以及具有文化智力的人,是最密集的,所以具有文化智力密集的地方,才能够和多样性结合,形成创新,这个也是我们说将来最有魅力、最有价值的城市空间和城市所必须遵循的道理。只有当科技让城市空间产生变革之后,才能够让共享空间促成连接的发生,而连接的发生才是产生文化多元性和文化创新最重要的推动力,共享生态让连接能够自形成。IP×IP 流量叠加科技提供了连接,科技提供了更多资源流动,最终形成的是社会的自由生态,像一个剧社就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自由生态,各种各样的自由生态会在科技和城市、科技和生活结合以后,越来越多的产生。文化智力在今天的科技和生活结合时,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IP 相乘,流量的叠加、IP 的相乘,会是今天产生更多价值点的地方。我们说从传统的招商逻辑,到充满创意精神的 IP 孵化跟集结地,是今天商业地产以及城市空间发展特别重要的思想方法。其实我们在做城市共享空间产品时,无论是共享办公、共享居住,还是生活共享,我最深切的感触是,这些城市都渴望着被重塑,而且的确需要被重塑,因为科技在喷薄,人们的思想越来越开放。所以,科技正在推动和改变着城市。 城市创造者的初心再造城市价值、建立共享文明规则、提升整体幸福力我看到过一组漫画, 上世纪50年代《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作者画过一组想象未来世界的漫画,60个场景。漫画里的城市综合体、新能源汽车(不靠油的汽车)、智慧腕表(带腕表就能测血压、心跳,掌握你的生命体征),这些场景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后成为了现实。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城市创造者,从一个建筑师开始,到开发商,去盖楼,今天我们作为内容创造者,在丰富城市的内容和房子,一直如此。 所以,今天的我希望能做好三件事。第一,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推动城市价值的再创造,再创造的人不是我,我们希望用空间的内容集结,再创造城市社区价值。第二,希望通过城市空间的再塑造、社群再造,推动共享文明规则的建立,共享文明规则我想是这个社会进步特别重要的价值。当这个社会越来越适应共享文明下的社会规则,我想我们大家会变得越来越舒服,越来越简单。第三,希望通过城市多元化空间的再造跟城市内容的集结和重塑,来为城市的创造力阶层提供更多整体幸福力提升的可能。我们创造的意义在于幸福力的升级和改造,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没有幸福力改造的科技和生活的结合,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场景的美好来源于生活幸福感的反射被科技所改变的场景将更有魅力。我们发现很多科技改造过的场景,智慧办公、智能楼宇,变成了思想频繁交流的集结地。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场景,场景的变化是科技所推动的,但场景的美好,是来源于生活中幸福感的反射,只有当幸福感反射在空间场景上,这个场景才是有价值的场景,而场景有价值,城市的空间才能有价值。在这里,我也想阐述我们这些拿 160 万亿平方米存量空间做改造素材的人,实际上我们心里是非常幸福的,因为我们利用科技和生活的结合,希望帮助更多的人提升他们的幸福力,我想这也一定是所有致力于创新的创业人群奋斗的最大原动力。毛大庆简介毛大庆,城市规划与区域经济学博士,优客工场创始人、董事长,优享创智创始人。中国科协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2015年3月,创办优客工场,目前在全球30座城市布局了超过100个场地。优客工场以构建国际一流的共享空间为目标,旨在打造为创新创业企业服务的加速器、科技成果转化及孵化平台,最终成为一个覆盖全产业链的商业社交平台。著有《城市人居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研究》、《永不可及的美好》、《无处安放的童年》、《一口气读懂新加坡》,译著《奔跑的力量》、《朝圣波士顿马拉松》、《鞋狗》、《为谁留的空椅子》《凿开公司间的隔栅》等。爱好马拉松运动,截止2018年6月,已经完成全程马拉松82个。文章选自优客工场,2018年7月31日
2018年8月1日 -
张燕生:中国经济正处于转折期,短期稳定是大局
专家简介张燕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内外风险交织在中国稳步推进去杠杆的关口。 去年以来,以非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住户部门的债务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进行测算的宏观杠杆率上升势头明显放缓。人民日报近日报道称,去杠杆初见成效,我国进入稳定杠杆阶段。 与此同时,世界政治经济环境更加错综复杂,美国用贸易壁垒推动”公平贸易”原则陡增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中国经济自身在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过程中也经历诸多“不良反应”。 今年7月中旬,去杠杆议题又引发央行和财政两大主力就谁该对地方高债务率负主要责任和谁该在稳增长政策上进一步发力的争论。这场争论和引发的讨论直到7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方才画上休止符。 7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财政金融政策要协同发力: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此外,还要加快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出资到位,加快出清“僵尸企业”等。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向澎湃新闻指出,中国在过去十年用加杠杆的方式给世界经济增长拉车,把世界从经济泥潭里拉出来,中国宏观杠杆率上升了114个百分点。继续增加宏观杠杆率只会让中国经济走向崩溃边缘。而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的实质是想要中国继续加杠杆,主动为美国赤字融资。 “中国提出决胜三年打三个攻坚战,第一个攻坚战就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最大的风险是金融、是货币和国际收支。金融和财政政策如何更好地协调形成合力,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近日,张燕生在北京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对中国经济形势发表看法。 他谈到,中国经济正处于转折期,短期稳定是大局,中期处理好结构性改革,长期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稳是基础、稳是大局、稳是关键,因此需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实现稳中求进。而实现中长期的目标,最少要坚持7到8年,把最困难的调整时间挺过去。 他强调,中国有最好的市场需求、最完备的产业体系和最高的储蓄率,中国经济正在发生质的变化,稳中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 “贸易战是美国想让中国继续加杠杆” 澎湃新闻:7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应对好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同时财政金融政策要协同发力,更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更有力服务宏观大局等。你对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内容如何解读? 张燕生: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现在处于明显的转折期。 先说投资。过去支撑我们快速增长的重大投资需求主力都已经过了峰值,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等峰值都可能已过。今后新的重大投资需求主力是什么,会不会是外商投资、民间投资、创新投资、绿色投资、民生投资?有可能。 2005年之前,外资主要是成本驱动型,到中国来获取低成本要素和资源,产品销往全球;2005年至2012年,外资主要是市场驱动型,这个时期中国GDP的基数比美国小得多,增量比美国大得多,引发内销的外资快速增加;但2012年以后,效率驱动型外资快速增长。在2012年前,70%的外资投入在一般制造、低端制造,2012年后逐渐变成70%投入在服务,还有一部分在高端制造。 这就面临一个问题,我国在高端服务、高端制造领域的资质、标准、规则、规范,跟国际通行标准的差距显著大于一般制造业,包括混合所有制的结构、效率和便利化也同样存在差距。面对这样的差距,我们需要的转变之大就像过去四十年所经历的那样,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改革开放和调整。 再说消费。我们这一代人是饿肚子长大的,我开玩笑说,我们这一代,有钱没钱也不消费,有好东西便宜东西总是买最便宜的。所以,消费者永远选择最便宜的而不是最好的,因此那个时代竞争就是低成本,“谁创新谁死”。当我们的孩子这一代成为消费主体的时候,他们是有钱没钱也消费,敢负债,有好东西便宜东西总是买最好的,这个时代是“谁不创新谁死”。我们孩子的下一代呢?他们的消费不仅仅是好东西,而是要个性、差异、创意、虚拟的消费。企业必须生产小批量、差异化、有文化含量和虚拟想像空间的产品。 中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以上人群,但是,从代工贴牌到自给,从简单模仿到创新,从价值链低端到高端,需要系统性调整和变革。 当前中国有两股劲,一股还停留在过去的模式、业态、结构,像温水煮青蛙;还有一股劲想往上走,但它一方面面临自身缺技术、缺人才、缺资金、缺品牌、缺渠道的转型之痛,另一方面也面临外部体系还是旧的体系。新旧交织、动能转换,中国经济在经历巨大转变。所有这些变化,最少需要7到8年才可能完成,也就是要到2025年。 从2008年到2017年,我们的宏观杠杆率上升了114个百分点,从141.3上升到255.7(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 外因是什么?外因就是美国需要中国“拉车”。 2009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重是1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50%;十年过去,中国的GDP占世界比重是15%,十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30%以上。也就是说,中国在过去十年是用加杠杆的方式给世界经济增长拉车,把世界经济从泥潭里拉出来。 如果未来再拉10年,杠杆率再增加114个点,恐怕那时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或者崩溃了。 什么是贸易战?贸易战就是美国想让中国继续拉车,继续加杠杆。 过去十年由于中国的贡献,把美国从经济泥潭中拉出来了。但是现在美国还有很多困难,又要加息、又要减税、又要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都会导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增加、财政赤字增加、债务率提高。这些调整的成本今天发生,收益要十年后发生,这十年美国会怎么做?贸易战就是要中国更多进口,外商企业及全球供应链要尽快回归美国,中国要主动为美国赤字融资。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决胜三年打三个攻坚战,第一个攻坚战就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最大的风险是金融,是货币和国际收支。金融和财政政策如何更好地协调形成合力,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我觉得政府过去的表述很准确,短期稳定是大局,中期处理好结构性改革,长期过去讲新常态,现在讲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稳是基础、稳是大局、稳是关键,因此需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实现稳中求进。而实现中长期目标,最少要坚持过7到8年的苦日子,把最困难的调整时间挺过去。 “中国要考虑大幅减税减负给企业提供更好的创新转型条件” 澎湃新闻:再说前段时间央行跟财政部较为公开化的政策讨论,你认为双方在去杠杆、稳增长上各自还有更多的政策空间、更有效的工具吗? 张燕生:对于中国的经济,有三句话讲得特别多,第一句话是中国经济潜力大,从汗水驱动转向智慧驱动的新旧动能转换,从低效率部门转向高效率部门的新旧结构转换,从市场政府对立模式转向市场政府和谐发力模式转换,就能够释放出巨大动能。 第二句话是中国经济韧性大,改革开放40年形成的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和冲击的统筹协调能力和差异性多样性结构,使中国经济抗风险和冲击的韧性大。 第三句话是中国经济的回旋余地大。中国经济的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分别处于创新驱动、投资驱动和资源驱动的不同发展阶段,东方不亮西方亮,经济回旋余地大。 我们不从总量增长看,从结构看、从创新看、从新经济比重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其实货币和财政政策只要保持连续性,政策协调保持一个很好的稳定性,创造一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宽松环境,中国经济的内在动力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需要危机冲击这样的极端选择。 2012年,中国经济进入减速阶段,GDP在2012年和2015年分别破“八”和“七”。在2014年8月美国经济触底、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时候,中国的宏观经济杠杆率是200多一点。这个时期和过去几年不同,2009年至2014年上半年,美国量化宽松的流动性无法转为美国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其中相当一部分流入中国形成了房地产和其他资产的泡沫。2015年美国第一次加息,国际资本开始大规模流回美国,流出中国,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外溢效应,对中国就是紧缩性质的影响。 中国现在真正面临的风险是美国要用贸易战的方式逼中国继续加杠杆。我们必须保持冷静和理性,你说我国企太大我改革国企,你说我市场准入门槛太高我降低,你说我知识产权保护不好我加强,有问题我改,而且主动推进高水平开放、高标准改革、高质量发展,但是我不加杠杆。美国加息,引发资本流入美国,美元有升值的压力,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有上升的压力,我做适应性调整;美国减税,财政赤字增加,我做适应性调整;美国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债务率进一步上升,我做适应性调整,但不在贸易战威胁下买单。 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有两个选择,一是增加负债放水,还有一个是减税减负。哪个更好一点呢? 我们整体的财政状况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从高速增长变成高质量发展,企业需要轻装上阵,企业需要资金创新和投资,因此中国要考虑的是大幅减税减负给企业提供更好的创新转型条件。这对政府来说会形成比较大的财政负担,这方面我们或许可以向特朗普政府学习,较大幅度为企业减税减负,美国没有这种财政承受能力,但是为了未来它不得不这么做,成本今天发生,收益十年后发生,谁来买单? 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应该继续改革开放,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提升我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样一来很多矛盾和问题就能够化解。 中国金融体系要“引狼入室、与狼共舞、培养狼性” 澎湃新闻:中国近期推出一连串扩大开放措施,扩大市场准入。金融领域的开放是风险特别大的,因为我们的金融体系还相对薄弱、金融人才和监管经验与华尔街相比也有差距,在金融开放过程中你认为要做好哪些工作? 张燕生:中国有一个优势,是高储蓄率国家,我们有世界最高的储蓄率和最大规模的储蓄资金,却没有办法实现从高储蓄率到高效率投资的转变。 高储蓄率和高效率投资的中间渠道是金融体系。如何解决金融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基于金融监管能力基础上的“引狼入室、与狼共舞、培养狼性”。 开放的本质是改革。开放会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引狼入室,但开放以后你能不能跑过狼?跑不过是可能会被狼吃掉的。你要想跑过狼,你要有狼性,就必须通过改革,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才能够活下来。 我们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就是,“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我还有一句话,英国和美国赢在开放、输在开放,中国怎么能够保证自己在开放中不输呢?核心是增强综合国力和提升国际竞争力。 中国的金融市场要进一步发展,需要三管齐下,第一能力建设,第二体制建设,第三跨境网络建设。这些是经验积累和能力提升的过程,是实践的过程。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用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促进内地现代金融体系发展,是一个重要课题。 澎湃新闻:怎样才能让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张燕生:美国经济曾经患上“美国病”。从1990年以来,美国高技术制造业率、中高技术制造业率持续下降,金融、房地产、建筑在美国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持续上升;2000至2007年美国发明专利增长率持续下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对优秀人才最有吸引力的职业是金融而不是创新,时间长了就成了“空心”。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GE(通用电气)进行了战略调整,逐步剥离金融和非核心业务,扩大实体和工业物联网等核心业务。我问GE的人,为什么把GE CAPITAL给卖了,GE金融在你的经营型利润所占的比重是41%啊?他说,“我们GE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我要成为百年老店就不能把金融当作主业,金融挣钱太快、太多、太容易。” 从2003年到2012年,这十年泡沫的繁荣,使每个人都很疯狂,有钱就买房,有钱就做资本经营,用金融的手段把一切都泡沫化。比如科技创新,像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影子都还没有,已经炒到天上去了,过度透支未来还怎么做科技创新呢?所以,经济学家们的提问,我叫“戈登之迷”,为什么新工业革命时代全球劳动生产力减速?现在在中国,金融板块和房地产板块在上市公司市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经高于美国泡沫经济最高的时期。 对政府来说,它要用各种办法来推动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怎样才能做到呢?怎样才能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首先要提高混合所有制结构效率水平。中国过去40年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它的所有制结构中,民企占61.2%,国企占27.8%,外企占11%,如果简化为经验系数,也就是0.6:0.3:0.1。 这样的比例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下一步会继续完善。这样的混合所有制结构能够保证充分竞争,就能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那么我们的金融能不能在提升金融监管水平和能力的基础上,构建相对均衡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呢? 对政府来说,什么是好的金融监管?我们是不知道的。 美国充满了金融创新、金融活力、金融市场交易和竞争力,但美国却把自己推向了虚拟泡沫和空心化。2009年,奥巴马在演讲中提到“岩上之屋”,中心思想就是美国再也不能把自己的经济大厦建立在金融、房地产和建筑的基础上。 市场经济就像个孩子,有它的不同成长阶段。中国市场改革从农贸市场开始,大概是3岁,到了商品市场是12岁,到了要素市场是15岁,到了金融市场是18岁。如果要市场成长得更好走得更远,政府监管能力也要同步提升。 中国很幸运有香港。香港是一个全球性的多层次国际资本市场,一个一流的直接融资市场,市场、法治和监管都比较成熟。可以让香港和内地之间有更多的监管、治理和制度交流合作,用好香港金融发展的经验教训。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过去四十年的经验看,凡是经济发展好的地方,从来不是市场大和小的问题,也不是政府强和弱的问题,政府、市场和社会需要形成合力,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我觉得核心还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经济内部在发生深刻变化” 澎湃新闻:有一些分析认为,2015年中国股灾的一个肇因是美国抽走资金。你认为,在贸易摩擦的背景之下,美国有没有可能再利用类似的金融手段? 张燕生:中国这样的国家没有谁能够用阴谋的方式打垮,唯一被打垮的可能只能是自己犯错误。 过去十年,我们的宏观杠杆率上升114个百分点是因为外部压力。从2008年一直到2015年,美国在搞量宽,欧洲在搞量宽,日本在搞量宽,他们量宽的钱到哪去了?这些钱既没有变成他们的消费也没有变成他们的投资。很大程度上,高杠杆率国家的钱都是去了低杠杆率的国家,把低杠杆率的国家炒成高杠杆率的国家,在泡沫中间把这些因高杠杆率而遇到危机的国家从泥潭里拖出来了。 因此,当2015年美国宣布经济见底,就要开始加息,钱就回去了。2015年美国资本净输入规模估计达4600亿美元,同比增长18.3%,占全球资本输入总额的38%。 对此,我们早就应该做好准备,如何让短期资本的流入和流出不形成危机或大的冲击。提出托宾税就是这个意思,让资本大规模的进和出有成本。 澎湃新闻:我们说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稳中有进,从你的角度看,中国经济未来的信心在哪里? 张燕生:第一,中国有世界第一大的市场和高成长性。大量中等收入以上人群,他们对品质有高要求,对差异化有高要求,对多样性有高要求,这些需求会引致企业必须要创新。因此,中国有最好的市场需求。 第二,中国有最完备的产业体系。 第三,中国有世界最高的储蓄率。 美国老是想阻挠中国高端技术和产业的发展,这是挡不住的。你不给中国技术,但绝大多数技术和科学知识都是公共物品。像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现在都是上百亿投向重大科学项目、基础研究项目,十年以后,这些结果就能够显现。 中国今天在发生的变化和过去完全不同性质,现在更多的是质变。我们有“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大国优势,这种差异化优势是外人根本读不懂的东西。他们老是看总量,看GDP、财政、货币,没有想过总量的内容其实在发生深刻变化。文章选自澎湃新闻网,2018年7月30日
2018年8月1日 -

【国际商报】 | CCG:中美可通过合作弥合分歧
中国和美国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关系事关两国乃至世界的稳定和繁荣发展。然而,当前的中美关系正遭受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困扰。7月24日,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发布了中美关系系列报告《理解与破局: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度分析和智库建议》。《报告》全面解析了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日益加剧的贸易摩擦对中美双方的影响,探讨了中美通过合作弥合分歧的潜在空间,并针对性地从中美经济结构、贸易统计方法、双边服务贸易合作和“二轨外交”等多个层面提出了十条化解贸易争端的应对之策。 发布会上,CCG主任王辉耀介绍道,《报告》旨在通过详实的数据和理性的分析,为笼罩在“贸易战”阴影下的中美双方消除误解、弥合分歧,以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CCG成立十年来积极发挥智库作用开展二轨外交,致力于推进中美关系互利共赢发展。近期,CCG智库代表团两次深入美国,与传统基金会、哈得逊研究所、外交关系委员会等主流智库以及美国国会议员、美国中国商会进行沟通,并与美国政商学代表进行了对话交流。 “美中贸易逆差从经济原理解释是全球经济迅速发展造成的结构性问题。”《报告》认为,从贸易经济原理和中美经贸往来的事实看,美中贸易逆差的形成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其一,正如“特里芬难题”预示,美中贸易逆差是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的必然结果。如果美国不维持贸易逆差,美元流动性缩减,将对全球贸易产生负面影响;其二,从宏观经济学原理来看,美国持续下降的居民储蓄和飙升的国债拉大了贸易差额。去年,美国居民储蓄率降至3.6%,联邦债务率超过了100%;其三,从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来看,现行国际分工体系决定了中美贸易格局。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密集性产业。中美双边贸易直接反映了两国在比较优势和经济结构上的互补性——在中美货物贸易中,美国是逆差,在中美服务贸易中,中国是逆差;其四,美国出口管制进一步拉大了美中贸易逆差。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7年4月的报告,如果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程度降低至对巴西的水平,对华贸易逆差最多可缩减24%;如果降到对法国的水平,双边逆差最多可消减34%。 同时,传统的统计方法对美中经贸逆差存在严重误判,采用提高贸易壁垒的保护主义方式解决不了逆差问题。”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美方贸易统计方法过于简单,而且实际上,在全球价值链中,贸易顺差反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反映在美国。“《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已是美国服务业出口的第二大目的地,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的美方统计为530亿美元(中方统计为547亿美元),但这部分服务贸易顺差被美国“忽略不计”。 然而,美国国内对贸易战的态度也是多元化的。政治家反对的声音日益强烈,美国参议院7月11日以88比11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总统关税权力,两党罕见展示一致立场。特朗普团队是否存在共识也引发外界猜测。此外,美国国内经济学家、零售商、行业协会、商业团体和美国员工等各界反对声日涨。反对特朗普中国贸易政策的农业州和有诸多跨国公司的州也不在少数。 CCG课题组认为,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是美中发生贸易摩擦的重要诱因。中美经济结构的转型是直接推动,新时代的“竞争—合作”关系导致关注重心的转移。中美利益深度交织,双方可以通过扩大增量缩小逆差,中美启动对话的可能性增大。“贸易战”好比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不符合中美两国长远利益,不但会对中国GDP增幅和继续深化改革造成一定影响,也将极大抵消中美贸易对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作出的重大贡献,其导致的成本升高和人才缺乏亦将阻碍美国科技创新。除了导致中美双方都无法全身而退,”贸易战”对于世界经济、多边规则和体系也将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7月24日,全球化智库(CCG)发布的《理解与破局: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度分析和智库建议》提出了化解贸易战的十条建议:化解贸易摩擦的十条建议一、中美在经济上都面临一些结构性挑战,中美需加快自身经济结构调整,从自身做起,在做大增量的基础上共同改善贸易不平衡现状。二、要创新中美贸易的统计方法,摈弃传统的和过时的贸易统计模式,中美间的贸易要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来计算,要包括服务贸易和美企在华投资收入等全面来看,更加精准、且公正公平地显示两国所获得的真正价值。三、中美两国服务贸易有巨大增长空间,可在旅游、留学、投资移民、专利费和第三方收入、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加强合作。四、加强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效应,推动美跨国公司等利益团体的共识。通过美国大型跨国公司、企业协会、智库、社会组织等团体与美国政界保持沟通。中国可加强与在贸易战中受到损失的美国跨国公司的沟通,了解其受损情况,形成共识,反馈到美国决策层,推动两国重新回到对话协商的轨道上来。五、加强中美两国省/州间在基建、新兴产业、气候、能源等领域的合作,鼓励地方加强与美国各州、市政府合作,适时举办中美省/州长年度峰会、中美市长年度峰会,成立中美州政府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建立合作平台和机制。六、中美两国都是世贸组织(WTO)成员,中国可以在WTO框架下对美国进行申诉,又可以进行谈判,增加商讨合作的空间。两国还可以依托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对知识产权保护进行协商。对于WTO无法覆盖的领域,应当通过中美双边谈判来解决。七、美国需要放宽出口限制,尤其是放宽包括高科技公司在内的对华出口,实现双方共赢,减少因出口限制带来的负面效果和不利于减少贸易逆差的局面。八、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是维护中美投资关系和经贸关系的重要制度基础。应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或新的中美贸易协定谈判,减少相互投资的障碍,增加彼此市场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九、维护全球多边机制、推动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推动亚太多边合作机制形成,加快区域多边自贸体系建设。中国未来可以考虑加入新的TPP。中美为全球治理增量,在国际人才组织、国际电子商务联盟、全球数字合作方面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十、发挥“二轨外交”的作用,促进双方沟通。提高对外交流水平,鼓励中美两国智库、贸易协会等民间组织、NGO发挥二轨外交作用,形成有效而灵活的沟通途径和对话机制,负责传递两方的声音,积极协助双方消除误解、弥合分歧并最终提出解决方案。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8年7月31日
2018年8月1日 -

[China Plus] Understanding Trump Tariffs: Globalization should be the solution
[Waching Online]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imposing punitive tariffs on 34 billion US dollars worth of Chinese imports as of July 6, 2018. Since then, China has taken retaliatory levies of the same amount to defend its interests. Statistics from the U.S. Census Bureau shows in 2017, the U.S. posted a $375.6 billion deficit in goods with China. Though the number is alarmingly huge, a Chinese expert points out the manufacturing products from China actually help keep the US inflation low for the last 15 to 20 years.Noting the trade indifference, Dr.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a think tank based in Beijing, says the issue has to be looked at on all fronts, rather than just on the amount of goods across the border.From China Plus, 2018-7-16
2018年8月1日 -

【CGTN】Michael Pillsbury: China, US have no other path but to engage
Michael Pillsbury was in Beijing on Monday for the launch of a joint research project between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and the Hudson Institute to study China-US trade relations in the past 40 years, where they went wrong, and how to improve their trade relations in the upcoming decades.What does Donald Trump and his trade policy look like in the eyes of a friend? Where is his trade conflict with China headed? Will the engagement policy still work given the escalating trade tensions?CGTN conducted an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former Pentagon official Michael Pillsbury, currently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er on Chinese Strategy at the Hudson Institute, to explore these issues. Mr. Pillsbury, the author of the bestselling book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and is listed as one of the 10 names "that matter on China policy" by Politico Magazine.Mr. Michael Pillsbury speaking at the launching meeting of of a joint research project on China-US trade in Beijing, July 30, 2018. /CCGCGTN: You helped President Trump during his transition into the White House. What are your impressions of him and his trade policy?Pillsbury: He’s a very brilliant leader. He asks for advice from people around him.He first wrote about China in his book ("The America We Deserve"), probably in the year 2000, 18 years ago. And it’s quite a lengthy description that China will be the biggest challenge to America. And he talked about specific issues, including trade. He has been very focused on China-US trade issues, during the campaign also. This is very different from other candidates for president.You might say it’s a unique trademark of President Trump to be so concerned about trade as a cause of a loss of American jobs. Most American economists don’t believe this. They don’t think trade deficit matters. Our mainstream media and think tanks criticize him all day long, making it very difficult for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to get a clear message about Trump, because of so many filters trying to spin negative stories about him.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gestures during an event at the US Steel Corp. Granite City Works facility in Granite City, Illinois, July 26, 2018. /VCG PhotoCGTN: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Pillsbury: No, the trade war has not begun. It’s a dispute. If it can be handled correctly by both sides, we will be in a new phase of Sino-US cooperation. We once called China and the US a G2, which meant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cooperating for global governance. This notion is still highly possibl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Beijing-Washington relations.CGTN: What has brought us to the trade dispute? How did we get here?Pillsbury: I’ve never seen such a challenge over the past 40 years. Since China and the U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in 1979, they have been engaging with each other despite ups and downs in their relationships. The trade clash might be an eruption of a perennial anti-China sentiment.There are basically three schools of thought on China back in the United States. First, there are nationalists who have been calling on the US government to contain a rising China, which, however, is not a majority view. Around 10 to 20 percent of anti-China Americans hold this view.Another perception on China is completely the opposite. They’ve been clamoring for the "China collapse" theory. The book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by Gordon G. Chang, published in 2001, was a bestseller back then. These people have a big say on China-US economic ties.The third school is trade skeptics, who tap into specific issues concerning trade. They are longing to see a new type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to be forged one day.Former US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and former Chinese Premier Zhou Enlai during Nixon’s visit to China in February 1972. /VCG PhotoCGTN: Can the two countries continue with the engagement policy which has defined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over the last four decades?Pillsbury: Yes, of course. There’s no other path. We are now in a dangerous period. But I’m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From CGTN, 2018-7-31
2018年8月1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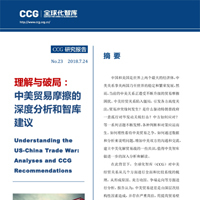
【China Watch】 | 10 suggestions on Sino-US trade friction
Since the United States imposed tariffs on Chinese goods on July 6, 2018, the bilateral trade friction has been escalating, affecting the prosperity of the global economy.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a think tank headquartered in Beijing, issued the analysis report “Understanding the Sino-US Trade War: Analyses and Recommendations”on July 24, 2018.The report is composed of four par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elements that caused the trade imbal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n analysis of motivations for launching the trade war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10 recommendations and, finally, outlook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According to the CCG report, the formation of Sino-US trade deficit root in the following reasons.First, the structural issue caused by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 trade deficit is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dollar’s domin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And in the view of macroeconomics, the US has seen continuous declinein household savings while national debt soaring, which have widened the trade ga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global value chain which determines the Sino-US trade pattern,US export control further widened the trade defici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Second,the traditional, simple statistical methodology has seriously misjudged the trade deficit, as the result is far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 report points out that in the current global value chain, China has the trade surplus, while the bulk of interest surplus is in the US. Third, changes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are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to promoting the trade friction.As for the motivation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o launch a trade war, the report points out that changes in the domestic 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the US, the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both China and the US, and the shifting focus of attention caused by the "competition-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in the new era are all important factors causing the Sino-US trade friction.The report points out that the trade war has not any long-term benefits for either country. It will not only affect China’s GDP growth and ongoing reform and economic upgrading, but also greatly offset th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from Chinese economic growthto the U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And it will also affect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s original function and even risk a great depression.Based on the analysis above, the report by CCG, aiming at defusing the trade wa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eries of recommendations:1. Both China and US need to accelerate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ir own economies, building in the foundation of domestic reform to bring out a joint improvement in the trade imbalance.2. The way that Sino-US trade is measured should be reformed and updated.3. China and US should work to expand bilateral trade in services, including tourism, education, exchange of talent, investment migr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e-commerce.4. All parties should work to restore and strengthen the role of economic ties as a bedrock i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This entails working through US multinationals to bring out a return to the track of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s.5. Strengthen Sino-US cooperation at the state/municipal level.6. Appeals and consult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within the WTOframework.7. The US could relax export restrictions, in particular concerning high-tech exports to China for a win-win goal.8. Revive talks towards the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 or explore a new Sino-US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to cutinvestment barriers on both sides and further open up markets.9. Promote free trade via facilitating regional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10. Both sides should work to strengthen the role of public diplomacy in facilitating bilateral exchanges.From China Watch,2018-7-30
2018年7月31日 -

【北京青年报】| 王辉耀:鼓励更多社会资源参与全球化人才培养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最近,清华大学学生全球胜任力发展指导中心顾问委员会向13名社会人士颁发了首批顾问委员聘书, 以此引入更多社会资源参与清华大学全球人才培养。“全球胜任力”是指在国际与多元文化环境中有效学习、工作和与人相处的能力。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并在全球事务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面对未来的机会和挑战,加强全球化人才培养是当务之急。 全球化人才培养仅仅依靠高校是不够的。高校的优势在于培养跨文化沟通的基础知识和素质,但在将知识付诸实践、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等方面亟待加强,很多高校在推进国际化办学上缺乏经费和资源支持。在这些方面,社会资源恰恰可以有效补位。如全球化智库(CCG)每年会吸引清华、北大、哈佛、牛津等国内外名校的学生来实习,2017年底联合东宇全球化人才发展基金会启动了“全球优秀实习生奖学金计划”,为国际人才提供高端的国际化研究、实践和交流平台,与知名国际机构、智库建立实习生交换项目,表现出色的实习生将获得奖学金。 在全球化人才培养上,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出现全球化人才匮乏的问题,日本文部科学省和经济产业省主导的全球化时代人才培养委员会发表了《产学官共同开展全球化人才培养》的报告,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也提出建议报告。日本政府经过参考和征询社会各界的意见,最终形成了国家层面的《全球化人才培养战略》。 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社会资源积极加入全球化人才培养。如日本经团联与政府合作,从2012年起每年选派30名大学生赴海外留学一年,每名学生获得100万日元奖学金。此外,经团联还组织相关企业举办留学生专场招聘会,吸收学成回国的人才。 40年前,邓小平提出要加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成千上万地派”,正式开启了新时期的出国留学工作。这是新中国大规模培养全球化人才的开端。4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迎来了留学潮和归国潮,聚集了一批全球化人才,但总体而言,我国的全球化人才数量还不够多,质量也不够高,尚不能满足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的需要。仅举一例:目前联合国系统的雇员中,中国籍雇员仅占1.12%,列第11位,居菲律宾、印度、俄罗斯等国之后,而中国向联合国缴纳的会费在各国缴纳会费总额中占比为7.921%,是缴纳会费第三多的国家。 在全球化人才培养上,还需要中国社会各界持续努力。首先,应制定国家层面的全球化人才培养战略,引导、激励和规范社会资源参与。当前,社会资源参与全球化人才培养没有形成一个完整有序的体系,政府应该鼓励社会各界进行讨论并听取有益建议,进而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国家层面的全球化人才培养战略,要坚持目标导向,培养适应中国发展需要的全球化人才;也要坚持问题导向,破除社会资源参与全球化人才培养的诸多障碍;要建立相应的引导、激励机制,构建多方参与、密切沟通的全球化人才培养体系。 其次,要吸引更多国际化的中国企业、中国智库和国际组织参与进来。“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和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智库,是青年立足中国了解世界的良好平台,而国际组织是青年以世界眼光观察中国的良好平台。在这些组织实习和锻炼,将培养中国青年完整的世界观和包容的心态。未来,可考虑建立统一平台发布中国企业、中国智库和国际组织的全球化人才实习岗位,评选最佳实习生雇主,推广相关经验,还可以考虑设置联合奖学金,资助优秀实习生继续深造。 再次,要推动中国学生与国际学生多交流。我国学生出国留学的主要目的地多为欧美发达国家,这导致中国学生对于西方国家的语言、文化比较熟悉,但西方国家不等于全球,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情况也需要中国学生了解,方能形成完整的世界观。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急需熟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况的人才,应鼓励更多中国学生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增进对这些国家语言、文化和综合国情的了解。 在持续鼓励出国留学的同时,还要加大来华留学工作力度。应鼓励国外青年学生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来华留学,与中国学生共同学习、生活;要鼓励社会资源举办各类民间交流活动,推动中外青年增进了解。“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只有中国青年真正具备了全球胜任力,中国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这需要更多社会资源参与全球化人才培养,在更大范围推动形成“立足中国,胜任全球”的共识。文章选自《北京青年报》,2018年7月29日
2018年7月31日